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国际贸易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从“关税对抗”阶段的贸易战1.0,到以技术封锁、规则排他和地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贸易战2.0,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壁垒显著加剧。
国联民生证券前瞻研究首席分析师、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执行总经理郭荆璞在《北大金融评论》发文表示,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和供应链重塑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既有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而是未来美国对第三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导致的在第三国投资的风险。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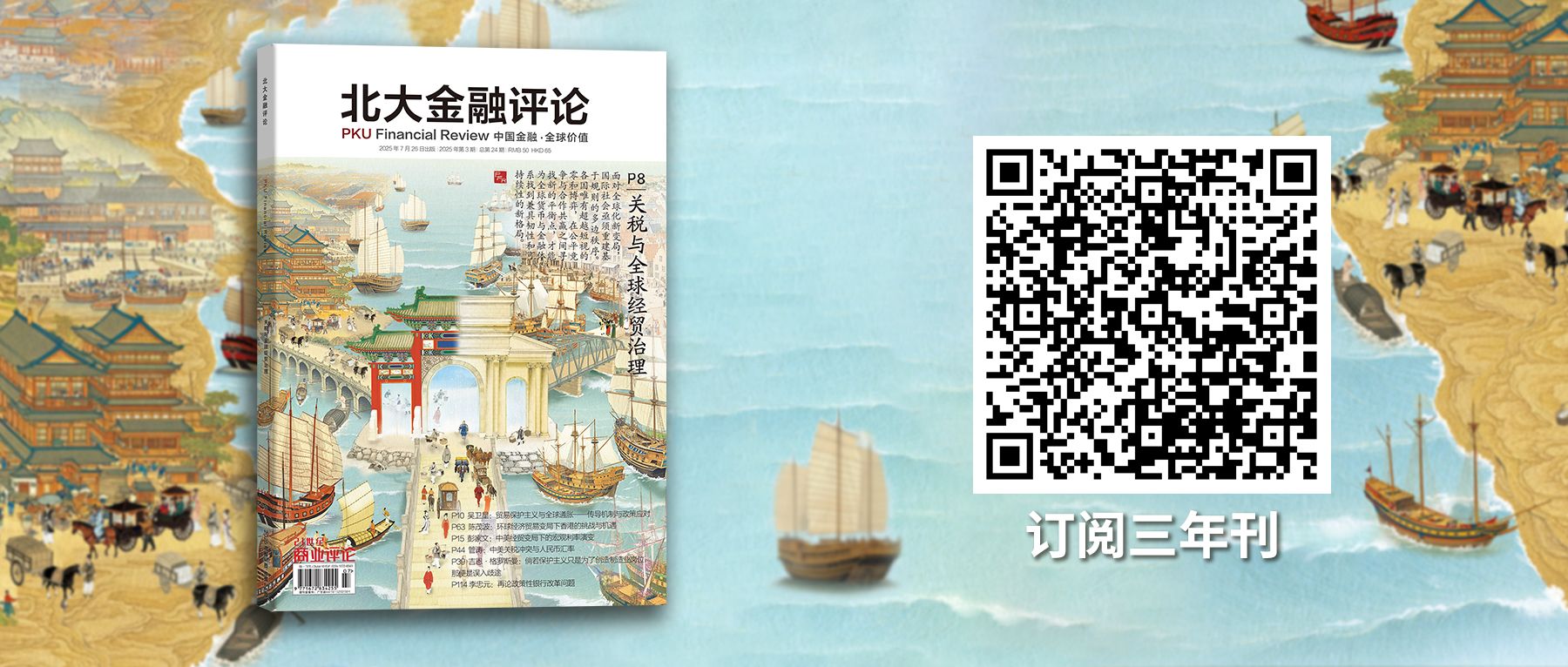
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国际贸易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从“关税对抗”阶段的贸易战1.0,到以技术封锁、规则排他和地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贸易战2.0,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壁垒显著加剧。美国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强化高技术限制和产业链从中国外移趋势,与此同时,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也纷纷跟进,形成“多边制华”的博弈格局。
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战、逆全球化和供应链重塑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既有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而是未来美国对第三国关税政策的随意性,导致的在第三国投资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同样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这种全球性战略博弈趋势不仅压缩了中国企业的传统外贸空间,更对其技术积累、品牌国际化和产业链韧性提出更高要求。贸易战的本质,已不再是简单的进出口纠纷,而是围绕全球产业主导权与技术生态控制权的长期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从战术应对转向战略转型,构建具有全球适应性与内生抗压能力的商业体系。
贸易战演进态势
自2018年起,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被称为“贸易战1.0”。这一阶段以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关税战为起点,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等领域的快速崛起,并试图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2018年7月,美国首次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范围不断扩大,累计涉及数千亿美元商品。中国则以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应对,涉及农产品、汽车、能源等多个领域。贸易战1.0的显著特征是“关税对关税”的直接对抗,导致全球供应链震荡,制造业信心下滑,两国经济增长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回顾历史,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以“草拟”“磋商”为主,均未出台针对性的制裁措施;第二阶段,由美方落地第一批关税加征清单开启,随后双方针对性贸易限制措施陆续出台并持续升级,此阶段美国发布三批关税加征清单,共涉及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最终以中美在G20峰会达成经贸共识结束,第二阶段期间权益市场震荡下行;第三阶段,在经过双方多轮经贸磋商后,美方加码贸易限制政策,摩擦再度升级,于2019年9月起再度走向缓和,在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白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摩擦1.0最终告一段落。

2020年初,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贸易战暂时降温,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分歧。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产业链逐渐形成“脱钩”趋势,2025年贸易战进入“2.0阶段”。此时贸易战不再局限于传统商品领域,而是向高科技、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扩展,表现出更强的战略性和制度性特征。贸易战由单一关税对抗向复合体系竞争转变。例如,美国通过《芯片科学法案》强化技术封锁,中国则以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实施精准反制。
由于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和不断上升的中国竞争力,经济领域的对比强化了美国的“零和思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陶坚指出,美国对“竞赢中国”的执念已经演变为“打压遏制”的实际行动。贸易战促使部分中国企业在过去6年中在美投资设厂,或逐步转向政治关系友好的第三国,然而随着美国关税政策在过去数个月之中不断转向,在部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国投资的风险也在急剧增加。
······
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订阅全年刊或三年刊
享独家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