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2024年里,一些带有明显的社会报复性质的恶性伤害犯罪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社交媒体用户义愤填膺地呼吁对行凶者严加惩罚,以儆效尤。那么,在数字时代,这种措施有用吗?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梁平汉在《北大金融评论》撰写随笔表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大大改变了社会治安形势。数字技术的发展固然提升了威慑效能,但这种提升本身并非万能。归根结底,潜在犯罪者能够被威慑,源于其对未来尚抱有希望,觉得不值得为了犯罪收益而铤而走险,放弃未来的合法收益。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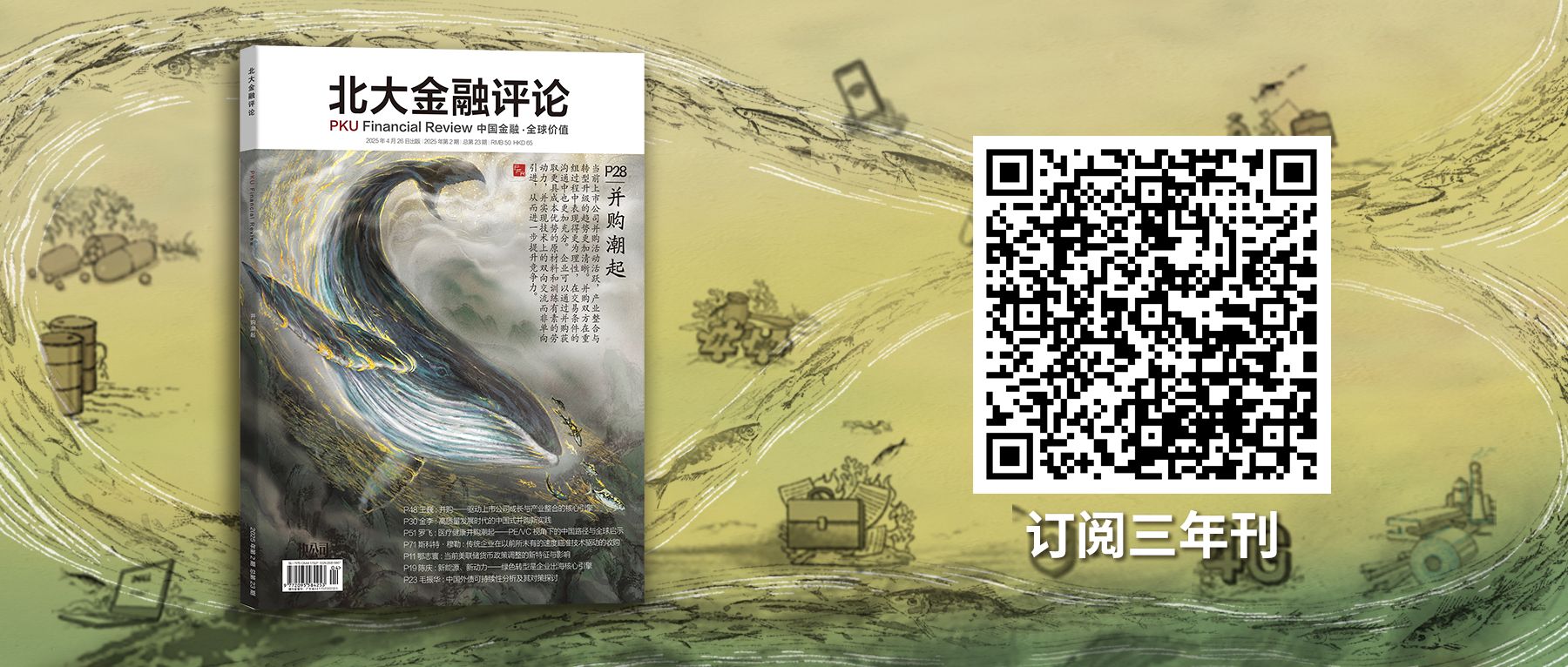
2024年里,一些带有明显的社会报复性质的恶性伤害犯罪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社交媒体用户义愤填膺地呼吁对行凶者严加惩罚,以儆效尤。那么,在数字时代,这种措施有用吗?
理性犯罪人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大大改变了社会治安形势。但是,关于犯罪产生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发生变化。每一起案件当然都有着其背后的特定原因,但是其产生背后也潜藏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分析社会原因并不是为犯罪者开脱,而是讨论其背后的社会规律,从普通公众的角度看则是趋利避害,防范风险。我们可以利用由意大利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肇始,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发扬光大的理性犯罪人理论对此进行剖析。
理性犯罪人理论认为,潜在犯罪者基于成本收益决定是否进行犯罪活动。具体而言,潜在犯罪者会考虑三个因素:从事犯罪活动的预期收益,预期的惩罚,以及从事犯罪活动后失去的劳动力市场机会(机会成本)。而其中预期的惩罚实际上又由两部分组成:惩罚的力度,以及犯罪后被查获的概率。预期的惩罚和犯罪的机会成本一起,也被称为威慑的力度。因此,如果潜在犯罪者从事犯罪活动的成本提升,也就是威慑力度加大,那么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更低。增大对犯罪者的惩罚力度就是一种加大威慑力度的举措,如2011年开始的“醉驾入刑”。但是,贝卡利亚对于刑罚效果就明确谈到“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后来的学术研究表明,相比于增大惩罚力度,提高犯罪后被查获的概率是更加有效的威慑手段。就是说,仅仅提高惩罚力度,并不能杜绝犯罪者的侥幸心理,而增大执法的确定性,保证“伸手必被捉”则更有威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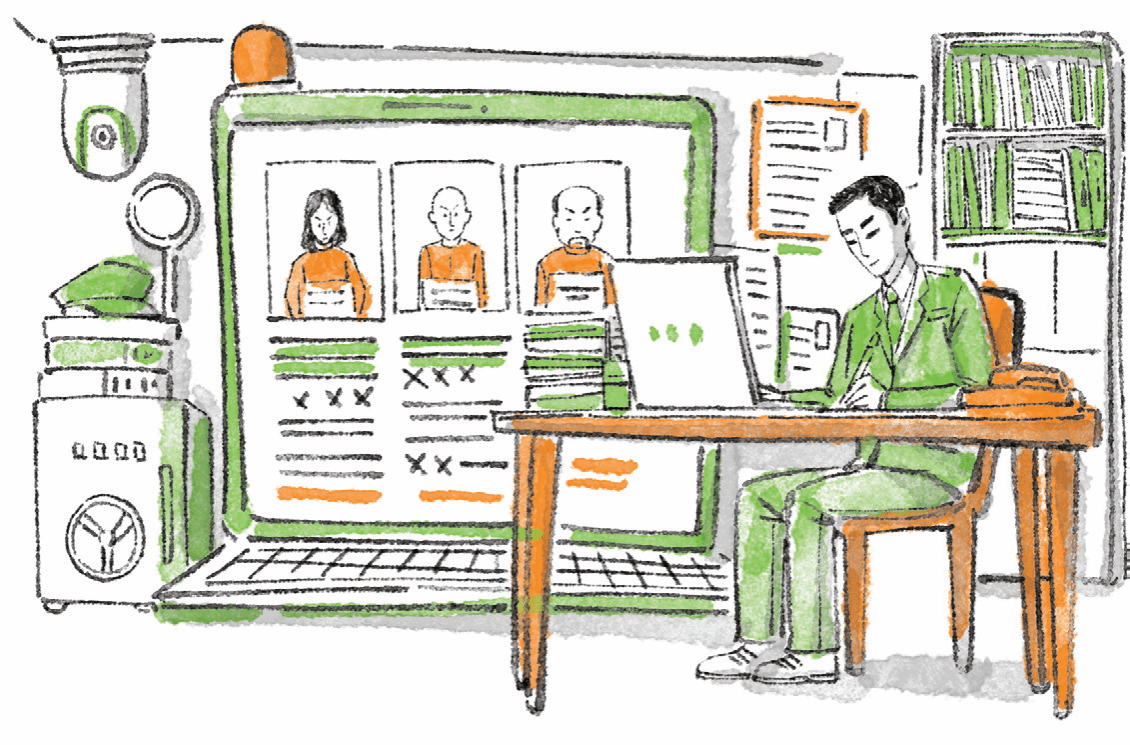
数字时代的犯罪变化
中国的社会治安形势在数字时代取得了很大改善,整体良好,这背后与中国司法体系强大的威慑力有着重要联系。一方面,广泛分布的公共视频安全设备构成了数字安全网络,弥补了警力的不足,大大提升了警方侦破案件的效率,增大了犯罪后被查获的概率。另一方面,各种“政审”措施限制了犯罪者及其直系亲属考公、参军及部分升学的机会,从而增大了犯罪的机会成本。除此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犯罪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笔者2022年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的一篇论文表明,移动支付的发展减少了社会中的现金使用频率,从而降低了盗窃犯罪的预期收益;同时各种新业态也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升了犯罪的机会成本。因此,移动支付的发展显著降低了盗窃犯罪发生率,产生了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这一切看上去是个完美的故事,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形态,增强了警方执法能力,强大的威慑力震慑了潜在犯罪者,使大家遵纪守法,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然而,如果放在博弈论的框架中,这一逻辑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固然理性的潜在犯罪者会对于威慑力度加大做出反应,在均衡时放弃犯罪的想法,但是如果遇到不理性或者一时想不开的潜在犯罪者怎么办?如果犯罪者的行为偏离了均衡路径,那么如何遏制犯罪呢?
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威慑犯罪行为和制止犯罪行为是两件密切相关,但是并非完全等同的事情。威慑犯罪是让理性犯罪者三思而行,在事前就放弃犯罪行为,而制止犯罪则是在犯罪现场阻止伤害扩大。如果我们以此分类方式看待中美司法体系,就会意识到中国威慑犯罪的能力很强,但是美国在制止犯罪上可能更胜一筹。原因无他,美国警方配枪,执法力量很强,民众的防护意识也不弱。
公共视频安全设备的广泛应用固然增大了威慑力度,但是对于制止犯罪并不是特别有效。人力仍然是社会治安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笔者尚未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的安全感而言,公共视频安全设备和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互补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其实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当犯罪人铤而走险时,摄像头就无能为力了,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及时出现的警察或者见义勇为的群众。因此,当下出现的一些恶性报复社会的犯罪案件,也许说明在社会治安体系建设中,不能仅仅关注威慑力量的建设,还要考虑在犯罪出现时如何进行应急处理,减少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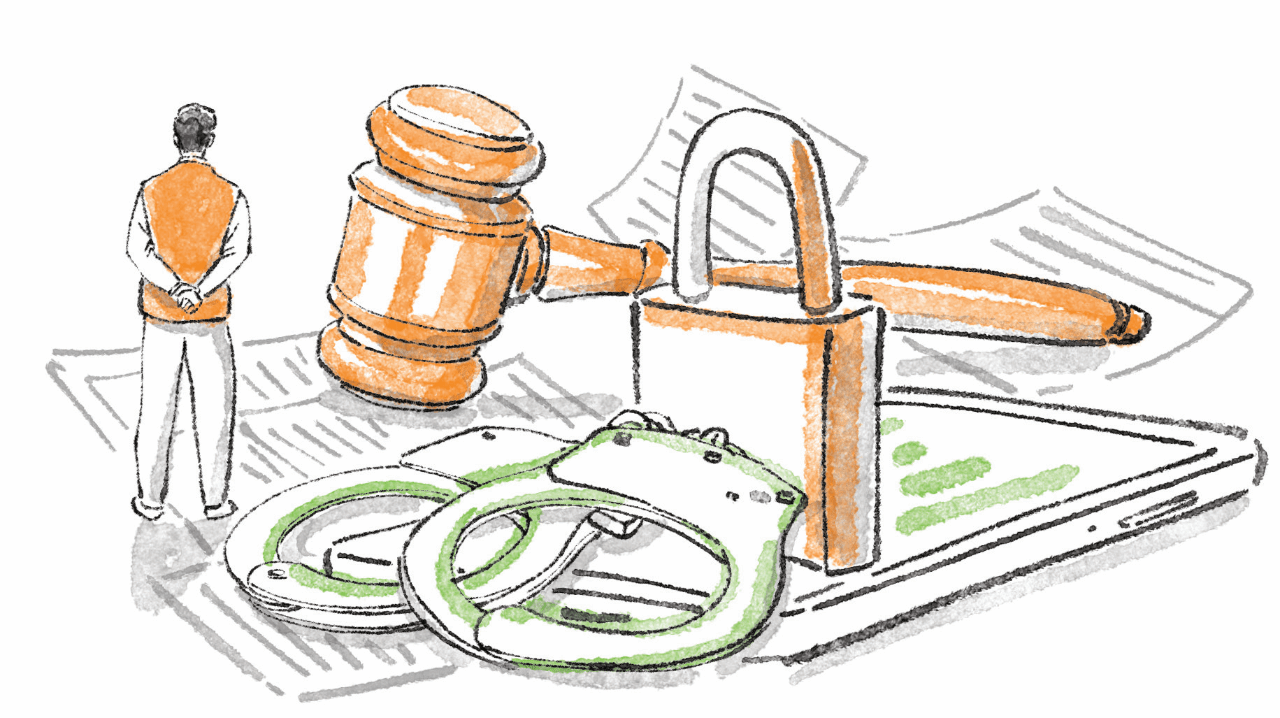
关键在于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和保障体系
数字技术的发展固然提升了威慑效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理性犯罪人理论框架中,就会发现这种提升本身并非万能。归根结底,潜在犯罪者能够被威慑,源于其对未来尚抱有希望,觉得不值得为了犯罪收益而铤而走险,放弃未来的合法收益。公共视频安全设备的使用固然提升了执法的确定性,但是对于犯罪的机会成本和犯罪收益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当下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实际上有所下降。这一点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特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其突出。对于一些中年失业的人来说,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的年龄歧视,其再就业机会较少。因此,其选择犯罪活动的劳动力市场损失较少。
不仅如此,一个不大为人知晓的事实是,现行的刑事惩罚力度对于中老年犯罪者的威慑作用并不那么强。现行的监狱劳改体制主要是针对中青年服刑人员设计,中老年犯人的劳动任务相对较轻,劳动效率也不高。而且,所有服刑人员的医疗费用均由财政承担,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在监狱中完全转化为财政负担。因此,入狱服刑对中老年犯罪者的威慑作用和改造作用相对更弱一些。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近年来减刑的大幅减少,以及醉驾等轻罪的大量出现,挤占了有限的监狱空间。这也降低了入狱服刑的威慑效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大量轻罪服刑人员挤占司法资源和监狱空间本身就是低效率的,这些资源和空间本来可以用来处理和关押社会危害更大的犯罪者。因此,靠严加惩罚,增加刑期来威慑犯罪者,且不说刑法修改本身的难度,就是从具体实施上看也是难有效果的。
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现行的监狱管理体制设计问题,现行的司法体系对于犯罪的威慑作用实际上有所下降。因此,数字技术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确实提升了对犯罪者的威慑效力,改善了社会治安,但是除此之外它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机器无法替代人类,关注个体的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社会治安起着更加基础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刑事司法体系中也存在优化空间,降低对于社会危害不大的轻罪的惩罚,避免对于现有资源的过多占用。社会公众也应该放弃重刑主义的想法,意识到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理解社会治安中的效率和成本。
原文标题:《数字时代的社会治安》
《北大金融评论》第23期已经上架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即享超值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