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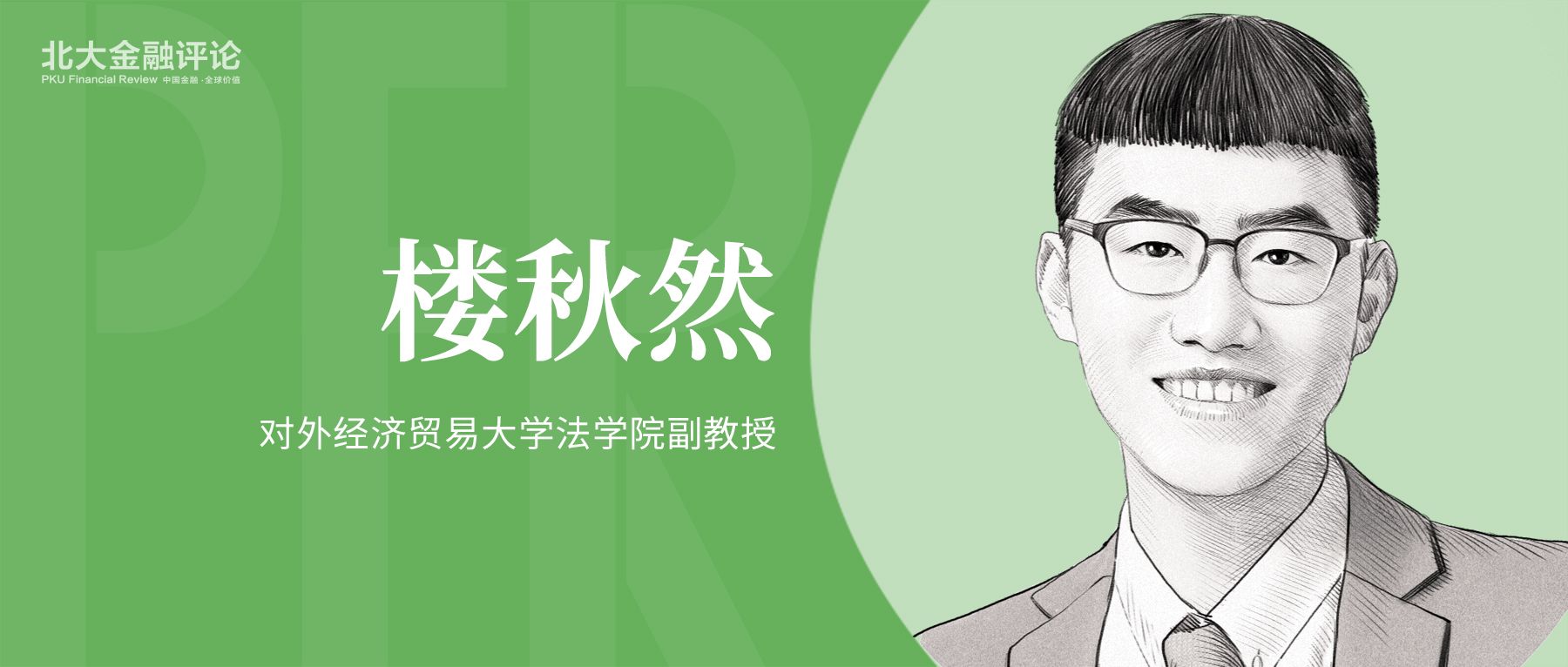

21世纪初,Hansmann和Kraakman两位教授预言,公司法的历史将会终结于股东至上主义。
言犹在耳,一场轰轰烈烈的ESG运动又开始推动公司法的转型进程。ESG运动最早可以上溯至16世纪贵格会教徒拒绝对赌博、军火营业投资的实践,但联合国于2006年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倡议则被普遍视为其现代开端。近年来,(上市)公司主动披露ESG信息、积极回应股东的环境与社会提案的实践大幅增加。量变最终引发了质变。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布宣言重述公司目的:公司不应当被视为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而应当承担向全体利益相关者传递价值的重大责任。
然而,与之类似的公司法理念大转向,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在2019年重述公司目的之前,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在1981年就曾经将公司的目的界定为向全体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仅仅16年之后,也就是在1997年,其便又改口称,公司的唯一目的乃在于最大化股东利润。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公司法时间”究竟是1981年还是真正的2024年?
似曾相识:公司的“公”“私”之争
在现代公司法的主流叙事中,公司乃是纯然的私人商业组织,追求的仅仅是股东利润的最大化。然而,公司法条文本身却从未作出过如此限定。这一规范性共识的形成,既脱胎于对公司法历史的选择性截取、规制对象的有意简化,也植根于公司法制度竞争的现实图景。
作为现代股份公司之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设立过程和经营方式,诠释了一段与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公司法历史。本应轻松拿下王室特许状的东印度公司,险些在1598年因为英国王室希望与西班牙实现和平而胎死腹中;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又得益于英、西和谈失败后,英国王室强调“普遍的海上通航自由”的政治诉求。而其所被赋予的包括宣战、统治殖民地等在内的各项“贸易特权”则更加彰显着其实现国家雄心而非单纯利润索取的定位。
这种公司法思想漂洋过海、跟随移民去到美国。其导致在20世纪之前,绝大多数设立的美国公司都或者本身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或者本质上符合国家的发展需要。而在进入20世纪之后直到70年代之前,美国的公司法理念又进入所谓的“管理者中心主义”的时代,股东利益或说公司利润也并未被视为公司的唯一甚至主要目标。其中,美苏冷战导致的意识形态之争,可能进一步促成了将公司视为提供社会福利的工具的想法。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滞胀现象、美股大熊市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股东至上主义方才浮出水面。
在现代的公司图景中,纯粹或说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也或许不是公司法的全部规制对象。在德国,职工人数超过2000人的公司需要适用“共决制”,即公司监事会的一半成员需要由职工选举产生。在日本,尽管麦克阿瑟曾经试图对日本公司进行美国化,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因素,日本公司最终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战时特征。主银行制度使得债权人的话语权不容小觑,交叉持股或说经联会使得管理层利益得到维护,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则切实保障了职工的利益,股东利益或说公司利润实现并非公司的唯一或说主要目的。
至于公司法的历史将会终结于股东至上主义的预言,则可能来源于对盎格鲁-撒克逊式公司治理模式之竞争力的自信。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受限、停滞,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法都开始学习美国。然而,依托比较法的改革与借鉴,并未导致公司法的彻底趋同。一方面,德国公司法继续保留其最具特色的共决制,甚至一度促成欧盟的相关公司法指令以强行法方式在所有成员国适用该制度(最后经妥协变为可选式)。另一方面,日本公司法尽管修法频仍、受美国法之强烈影响,但“仍不断强化日本独自的特色发展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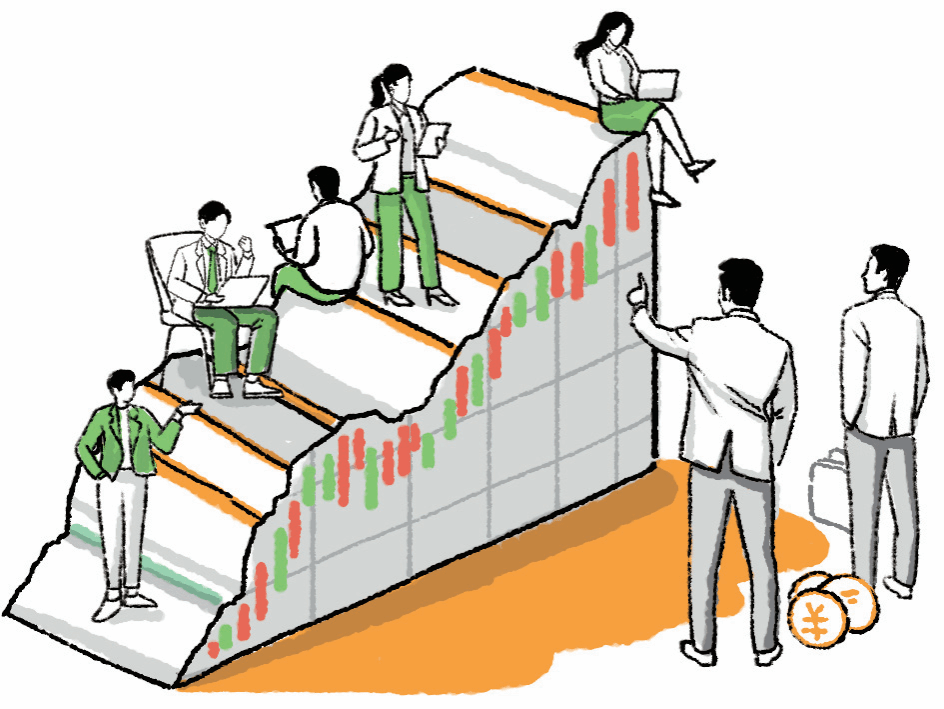
虚妄之词还是真心实意?
除去与主流叙事之间的显见隔阂,ESG运动在美国还遭受了另外两种基于“技术”的质疑。
Bebchuk和Tallarita的调查发现,尽管CEO们在2019年的商业圆桌会议宣言上签名,但是这些公司中有98%在事后没有将该宣言交付董事会决议。这或者意味着这些公司不认为这一宣言重要,或者意味着这一宣言事实上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公司经营。然而,后续发展却表明,ESG可能真的在被这些公司认真对待。Fairfax的研究显示,在财富100排行榜上排名前五十的公司中,超过86%的公司有至少一个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专门负责ESG的落实。另外,实证研究显示,超过53%的标普100公司、超过62%的财富200公司都已经在高管的激励薪酬中添加了ESG指标。
针对鼓吹ESG的机构投资者,反对者提出了如下假设。以BlackRock、Vanguard、StateStreet等为首的机构投资者如此热衷于ESG,无非是试图通过作秀以吸引对环境、社会议题尤其关心的千禧一代投资者。然而,事实可能未必如此。千禧一代对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浓厚兴趣,已经为世人皆知。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他们获取信息、发现真相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机构投资者仅仅通过作秀就可以愚弄这些投资者的可能性其实不大。而在排除对石化企业的投资、大力支持包括“Black Lives Matter”和“Me Too”在内的社会性议题的解决方面,机构投资者已经直接和大公司、公司高管站在了对立面。在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劝诫甚至威胁时,机构投资者也没有在ESG问题上有所退缩。这无疑进一步驳斥了机构投资者纯属作秀的主张。
在诚意问题之外,反对者们也怀疑ESG运动缺乏健全的配套制度,可能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司的ESG表现难以进行外部评价,导致投资者、监管者很难识别“漂绿”行为,从而出现资源错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然而,这些问题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在统一的会计准则形成之前,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不统一、不可比与如今的ESG信息披露相比可以说是不遑多让。而即便是在统一准则形成之后,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巨大弹性和易于操纵也酿成了不知多少公司治理丑闻。若此,不能仅仅因为ESG信息披露和评级仍处于起步阶段,就认为ESG运动本身不应被实现。
退潮时刻?
如火如荼的ESG运动正在遭受越多越多的质疑,以至于有人已经开始怀疑其是否已到退潮时刻。退潮的一大例证,即在于美国各州近些年来出台了不少所谓的“反ESG法案”。对于这一点,或许可以做以下两点回应。
一方面,仅就美国的情况来看,谈论ESG运动已经退潮或许为时尚早。首先,这些反ESG法案在限制机构投资者进行ESG投资的力度上差异明显,恐怕难以从根本上(即资金来源)扼住机构投资者的咽喉。其次,在强调ESG应与公司财务表现具有“重大性”关联、气候变化和平权运动已经成为全社会之重大关切的背景下,反ESG法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公司自觉配合ESG运动恐怕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一方面,跳脱出美国的特有政治环境和商业文化背景,反ESG在世界其他法域目前并未得到多少响应。例如,在中国,由于作为重要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公司目的上本就呈现“多元化”、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企业文化强调“仁”与“亲”,ESG而非反ESG恐怕更能得到认同。正因如此,对于ESG已经退潮的担忧恐怕并不成立。
进一步追问,ESG运动会不会终有退潮之时?公司法本身的演化似乎提示着我们,公司法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对于这种显见的公司法循环,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于:不同的公司法理念只是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工具;人们对该种公司法理念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所投射的希望的大小、该种公司法理念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实际能力,决定了该种理念持续的时间;当人们对其仍然满意时,其继续存在,反之,则钟摆将会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若此,ESG运动应当如何避免自己退潮?
在毛利文化中,有句谚语:世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是人,还是人!对于公司法的循环而言,亦复如是。社会公众对于特定社会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关注持久度将会决定某一公司法范式的生命力。社会公众究竟是更加关注利润获取,还是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决定了ESG运动的走向。尽管认为机构投资者纯属作秀的观点有待商榷,然而认为机构投资者积极投身ESG运动是为了“拉拢”千禧一代的说法则切中肯綮。与婴儿潮一代、X世代相比,千禧一代被普遍认为更加关注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解决。很多研究甚至认为,在千禧一代的投资观念中,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等于甚至高于投资回报。千禧一代的投资理念和(可能)掌握的财富规模,很好地解释了机构投资者在环境和社会议题上愿意与大公司分庭抗礼的原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比千禧一代年龄更小的Z世代似乎更加关心环境和社会议题,更加愿意在这些议题上发声。倘若这些研究和统计所言不虚、全球政治与经济环境不发生巨变,ESG运动恐怕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退潮。
公司法、公司治理机制本身能否实现适当的改革,从而确保其能够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同样决定了ESG运动退潮的速度。首先,高管的激励薪酬应当更多地与ESG指标相挂钩。一种简单的改革方案在于:ESG指标的实现或者特定ESG评级的达成,将可以决定高管所能获得的绩效目标收益。这种改革可以促成高管自觉落实ESG,但是其必须辅之以相关薪酬安排之全部信息的公开、详细披露,否则难以确保其有效性。其次,在高管薪酬之外,公司法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更为激进、彻底的改革。例如,公司法应当赋予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以派生诉讼权等可能极为重要。
最后,在将希望寄托于公司内部治理的同时,ESG运动的支持者们也不应该在争取针对ESG问题的专门立法上有所懈怠。在美国,机构投资者们“放弃”推动专门立法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已经失去直接介入的意愿和能力。而在其他法域例如中国,这一问题并不存在。
当投资者仍对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有所期待,而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专门立法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和社会问题时,对ESG运动的失望或许根本不会产生,或许会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公司法的循环也就或许存在被打破的可能。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即享超值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