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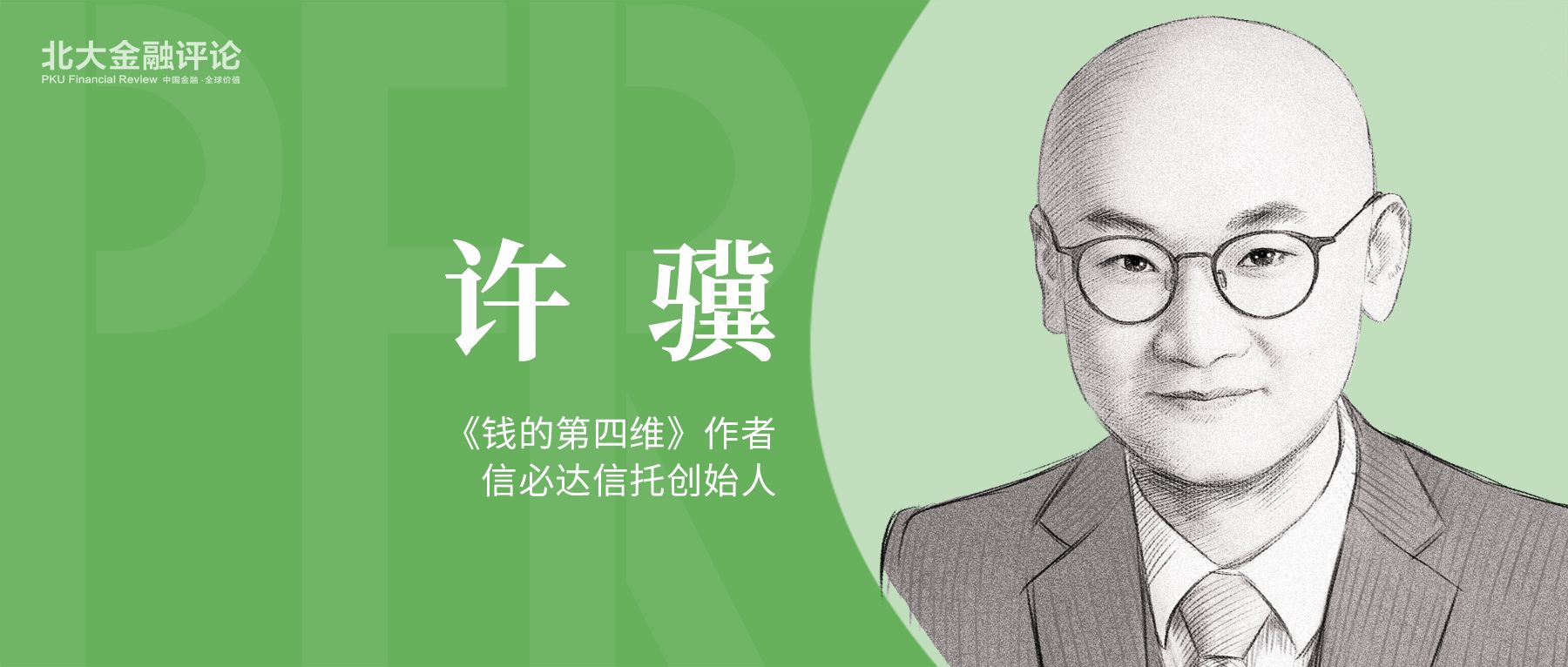

前不久,笔者与盛品儒小叙。众所周知,盛品儒是被称为“晚清三大商人”之一盛宣怀的曾孙(另外两位大商人分别是胡雪岩和张骞)。经盛品儒提醒,笔者方知今年是盛宣怀诞辰180周年。盛宣怀的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在半个世纪的沉浮中,他创造了天量财富。与他同时代的人(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胡雪岩等)倒下了,而盛宣怀却在一次次筛洗中得以保全,尤其是他所创立的事业留存至今,并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而盛宣怀家族在历史的演进中,已经传至六代,究竟有什么秘诀?盛品儒告诉笔者:传承的第一要务乃是“慈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重读盛宣怀,对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承者而言,或许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商贾,每不乐与官相交涉”
人们通常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经创下11个“第一”,比如:第一个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第一个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中国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等等。其实,盛宣怀还有第12个“第一”,那便是:中国第一个家族慈善信托。后世为何少有提起?且容我慢慢道来。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百多年前。1916年4月26日夜10点半,盛宣怀向他的亲信顾咏铨交代后事:“医生以我病无可救,嘱我预为吩咐。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份开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举我遗命,诰诫责备。”盛宣怀此处所谓“留作慈善”者,就是著名的被誉为“中国第一家族信托”的“愚斋义庄”。盛宣怀自1870年入仕,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至1916年去世,凡46年,慈善是他最后的遗愿。盛宣怀去世后,其子盛恩颐等人编撰的《行述》称:“(盛宣怀)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换言之,在盛宣怀心中,慈善是其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盛氏乃官宦世家,早在盛宣怀之前,其祖父盛隆是举人,父亲盛康是进士。盛家受范仲淹创立义庄,范氏一脉“百年不辍,薪火相传”的经历所吸引,早在盛康主事时,便于1867年创立了“拙园义庄”。所以和当代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盛宣怀做慈善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解不同,笔者认为,到盛宣怀这代,“慈善”在盛家已是传承了数十年的常识。这种常识,即便到今日仍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历史学家王尔敏在《盛宣怀与中国实业权利之维护》中曾说:“在晚清时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工商实业之提升地位,扩大影响,其有效途径多恃救灾报效银两,由此取得官阶,逐步上升。”这个说法,属于典型的恶意揣度。与很多人对传统商人热衷于巴结官员的印象不同,曾国藩早就写下了这样的观察:“中国商贾,每不乐与官相交涉。”就盛宣怀和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其实并非盛宣怀为了仕途去赈灾,恰恰相反,是赈灾确需专人去办,而这人正是盛宣怀。例如,光绪初年发生丁戊奇荒,全国饿殍千万,当时李鸿章面对“洋务、军务、赈务”之间互相“抢钱”的困境。赈务当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迫在眉睫之事。谁去开源办赈?盛宣怀临危受命,在江南募集善款善资,立了大功,方得李鸿章青睐。
在盛宣怀的一生中,类似的需要他出手赈灾的情况屡有发生,直到民国时期还一再上演。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的盛宣怀回国。各地因战乱而产生的灾民无算,由于亟需盛宣怀赈灾,临时政府将革命党查没的盛家资产还给他。盛宣怀如是方能向银行抵押家产贷出30万元,用于赈灾。当时只有盛宣怀在赈务方面累积了大量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堪当大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必须在创造它的“主人”的手中,才能活化及发挥其价值,强行占有的逻辑当时已经行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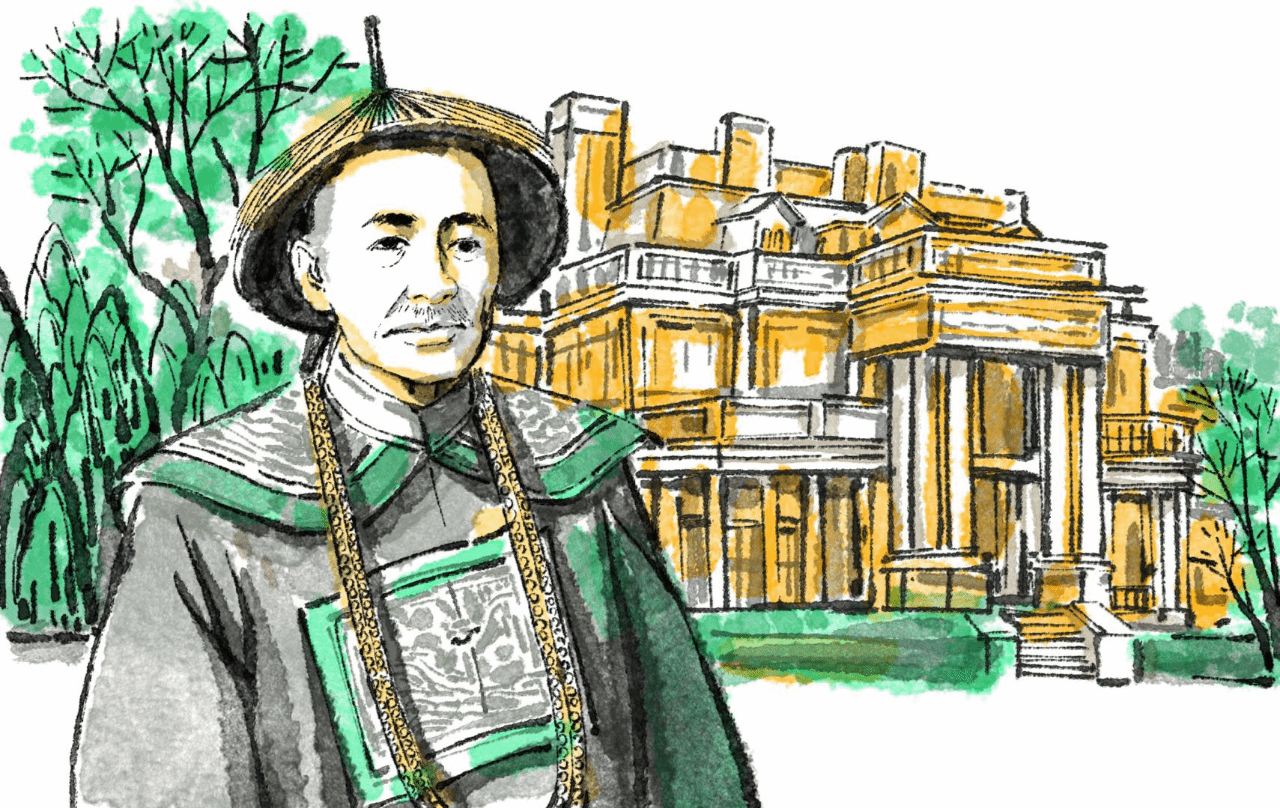
差点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庭抗礼
盛宣怀是近代独一无二的存在,可能是长期的实践令他洞察到:慈善是超然于政治、超然于国家的事业。基于此,盛宣怀成为清末民初的“常青树”。我们经常讲的“传承”是一个词,其实存在两个互动的主体,即:传富者和承富者。承富者很难尽悉传富者的付出和经历,因此传富者通常要考虑得更多。每个传富者的事业都需要基本盘,而盛宣怀则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方案,笔者称之为“慈善+”。“慈善+实业”,“慈善+教育”,“慈善+银行”等等,可以说,万物皆可与慈善结合。而通过慈善,盛宣怀获得了诸多收益,尤其以人脉最有价值,李鸿章、郑观应(《盛世危言》作者)、严信厚(“宁波帮”鼻祖)、沈敦和(另一位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等等,都是盛宣怀通过慈善事业深交并且结下不解之缘的。
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作为前清要员的盛宣怀,能继续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与其慈善事业有很大关系。《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的作者,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浒说:“盛宣怀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后回归社会,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依附袁世凯,也不是单纯依靠恢复实业家的身份……在盛宣怀洗白社会身份的过程中,实业之外的社会资源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诸如江皖水灾和南京兵灾等灾荒事件的发生,使得革命与建设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落差,也使得盛宣怀在赈灾方面的既有声望和潜在能力,成为极富价值的社会资源。”
根据笔者阅读的材料,盛宣怀大体将其遗产进行了以下三重分配:
一、先行拨付部分财产,用于安置两位遗孀(继室庄德华70万两,妾室萧氏30万两),安排女性后辈嫁妆(女儿嫁妆6万两,孙女3万两)。
二、剩余1160万两遗产对半分为两部分:分析股与保存股。其中,分析股是留给五房均分的遗产,保存股用于设立综合目的的家族信托。
三、价值580万两的保存股,又被均分为十股。其中四股为“善举准备金”(即真正用于义抚饥馑、水灾、旱荒、疫疠、地震及天灾等慈善活动的本金),四股为“本支准备金”(用于祭祀、宗祠建设、购置义田等盛氏宗族活动),另外两股为“公共开支准备金”(用于基金日常运营费用,如董事会经办费用)。
无独有偶,东西方的慈善事业,发生了神奇的回响。几乎与盛宣怀创立愚斋义庄的同时,1913年,大洋彼岸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盛宣怀或许也研究参考了西方家族慈善模式的精髓。比如,他指定李经方(李鸿章之子)作为监督人,并联合盛氏家族的五个分支及其他亲属,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同时制定了明确的管理章程。章程规定,管理委员会必须遵守“动用收益,不动用本金”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能使用财产的投资收益进行日常运作,严禁变卖或动用义庄的核心资产。可惜的是,由于下一代没有遵从祖训,加上当时总体法律环境不健全,导致义庄仅运营15年时间,便因家族内部产生纷争而正式解散。现代家族慈善信托在中国的首次实践,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不过值得首肯的是,愚斋义庄的创新尝试开创了全新的传承精神,具备标杆意义。而盛家延续至今的慈善精神,亦与此不无关系。笔者认为,如果盛家二代能够遵守祖训并发扬光大,愚斋义庄其实有机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庭抗礼,成为分别代表东西方的两支标志性民间慈善团体,此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盛宣怀的故事,值得当今的传承者反复琢磨。财富的道路上,创富、传富、承富;再创富、再传福、再承富……这是个生生不息的进程。只要音乐没停,舞就要一直跳下去。不断出现的新兴阶层,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要具备相当程度的新陈代谢能力,不断演化,才能穿越时代的藩篱,实现有效的传承。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财富的累积已经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在“共同富裕”的号召下,慈善将成为传承者新时代的主题之一,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盛宣怀命题”。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即享超值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