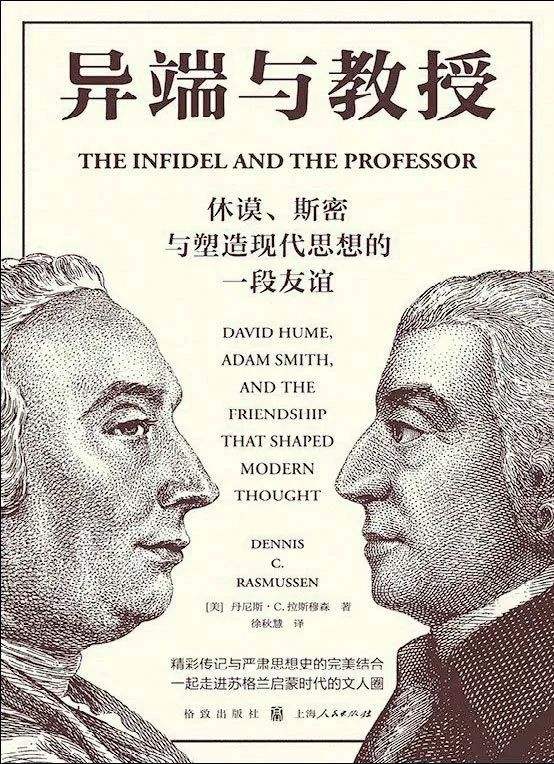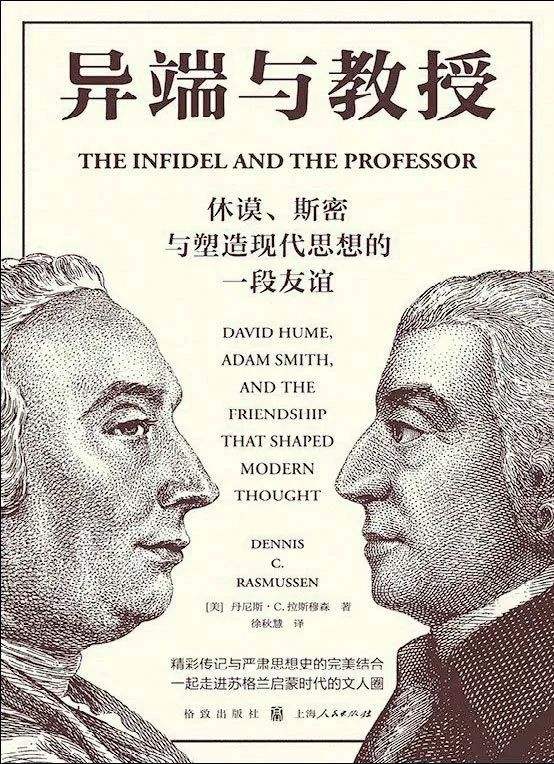斯密如何向休谟的人生和著述致敬?
1776年,休谟去世以后,斯密的《国富论》声名日隆,从国际名望和学术影响力来说,亚当·斯密俨然成为苏格兰文人圈当仁不让的学术领袖。巧合的是,休谟去世后不久,斯密就动身来到了休谟生活和奋斗了几十年的爱丁堡。彼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巨著,也希望离开相对偏僻安静的柯科迪。1778年1月,斯密定居爱丁堡,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岁月,仅仅在1782年和1787年两次短暂旅居伦敦,每次都待了4个月。
斯密最终决定定居爱丁堡是因为1778年获得的一份新工作。在《国富论》出版以后,斯密做了10年的海关专员,这事其实挺令后人不解和困惑的。这也就是说,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贸易捍卫者,为他的君主政府全职征收关税长达10年。确实如此,斯密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才获得这个职位。这次职位变动细究起来,其实也顺理成章。首先,做海关专员看似是其家族传承,斯密的几位亲戚和他父亲都是海关专员,而且他似乎精于此道,并对海关专员的工作内容兴趣盎然。另外,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绝非简单地反对所有关税。恰恰相反,他认为关税是大英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斯密反对的是把关税当作实现垄断的工具,或者是促进国内产业出口的工具。他并不反对适度、公平、用于必要财政支出的关税。必要的财政支出包括用于国防安全、司法行政和公共物品的支出。这份工作并非一份闲职,至少斯密自己不是这样看待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职位“每天都要按时上下班”,但他也发现,这份工作“不但轻松,而且深受人尊重,就我的生活方式而言,这个职位收益丰厚”。斯密唯一的遗憾是:“办公室里必不可少的行政工作打断了我的文学追求。”
在爱丁堡的这些年,斯密居住在潘缪尔府邸(Panmure House),这是位于修士门的一栋L形的简朴建筑,正好处于今天的皇家英里大道的最东头。这条街上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就是斯密的宅邸(这座房子现在已经成为访客和活动中心)。和过去一样,斯密和他的母亲和表姐妹生活在一起。他的母亲一直到1784年才以90岁高龄去世,而他的表姐妹珍妮特·道格拉斯早在斯密任职格拉斯哥大学时,就开始担当管家之职。定居爱丁堡后不久,表姐妹道格拉斯的小儿子,9岁的大卫·道格拉斯,也搬过来同住,后来他成了斯密的遗产继承人。
在定居爱丁堡之前,斯密从来没有在爱丁堡长时间居住过,甚至从未特意关注过这座城市,但自从搬过来以后,他很快就变成了爱丁堡家喻户晓的人物。游客们络绎不绝想拜访结识他,而城市精英们则热切渴望能与他高谈阔论。斯密填补了由于休谟离世而空缺的社交主人的位置。杜格尔·斯图尔特说,他有“一张简朴而热情好客的大桌子,他喜欢朋友们不邀而至,坐在一起随意畅谈”。斯密协助建立了名为“牡蛎俱乐部”(Oyster Club)的每周一次的晚餐会,这个俱乐部有时也被称为“亚当·斯密俱乐部”俱乐部的主要创建者还有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后者后来成为斯密的遗稿保管人。这三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三巨头,正如同约翰·雷所记述的,斯密、布莱克、赫顿分别是现代经济学、化学和地质学的创建者。这些人来人往、谈笑风生的社交生活肯定有助于减轻斯密痛失休谟之苦,但是也无法完全消除对休谟的思念。1784年,斯密对斯特拉恩说:“在这个世上,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新结交的那些友人无法替代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几年之后,斯密在和斯特拉恩的搭档托马斯·卡德尔通信时,话语中仍然散发着淡淡的哀伤。那是他为约翰·布鲁斯(John Bruce)的道德哲学著作写的推荐信,他写道:“他和我之间稍有不同,就如同我和休谟之间一样。我希望这本著作能为他带来极高的声誉。”休谟的名字和思想经常出现在牡蛎俱乐部的谈话中,就如同休谟就是牡蛎俱乐部的一员一样。奥地利医生和自由思想者弗朗索瓦.沙维尔.施韦迪奥尔(Francois Xavier Schwediauer),曾经自以为是地对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说:“斯密是已故的大卫·休谟最亲密的朋友,秉持和休谟同样的思想原则。”
海关工作占用了斯密大部分的时间,但他仍坚持写作。休谟去世后不久,当他还在柯科迪居住时,他就开始撰写一部有关他称之为“模仿的艺术”的著作,这一艺术门类包括诗歌、绘画、雕塑、舞蹈和音乐。尽管他在1778年时曾向格拉斯哥文学会宣读过几篇该主题的论文,但他终究没能完成这部著作,他所起草的这几篇论文在他去世后被编纂在《哲学论文集》中出版。斯密曾一度变得雄心勃勃。1785年,他在写给他人的信中称,他有两部“正在筹划中的大作”,一部是“关于文学的各个分支,关于哲学、诗歌和口才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他说:“有关这两部著作的文献资料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而且必要的梳理也已经完成。”但是,他对这种雄心壮志也有所保留:“年老体衰带来的精神怠惰越来越明显,我必须得使劲对抗这种变化。最终是否能完成这两部著作,现在还完全不能确定。”这话一语成谶,斯密的雄心最终化为泡影,两部著作均未如期如愿地完成。和休谟晚年时期一样,斯密也继续修订以前完成的那些著作。《国富论》第二版在1778年出版,其中增补和修改了部分内容。《国富论》第三版在1784年出版,其中的内容更加详实和丰富,多数增补内容出现在第四篇中,主要是斯密对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的批判性分析。斯密告诉斯特拉恩,这些增补内容包括:“对谷物出口奖金提出一些新反对意见;对捕捞白鲱鱼的渔船按照吨位发放奖金提出的反对意见;增加了一章用于论述商业系统;阐述特许贸易公司的简短历史,并全面阐述其荒谬和危害”;以及最重要的,针对东印度公司的论述。
与此同时,《国富论》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学界和公众,斯密当仁不让地成为首位自由贸易倡导者,这并非说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由贸易的人,而是说他是第一个突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并构建其过去所缺乏的理论地位的人。根据白哲特的评论,在《国富论》出版之前,自由贸易是“令人尊敬的父母在劝诫自己的孩子时可能会反对的原则”,尽管“它被看作是诱惑人心的异端邪说,但反对它的告诫是必要的”。《国富论》出版后不出10年,这种异端邪说就成为政府颁布的正式官方政策。世间流传着无数有关斯密的故事,刚好有个故事很好地描述了斯密彼时所受到的礼遇。1787年,斯密到访伦敦,当他来到时任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房间时,房间里除了皮特之外,还有几位高级大臣,所有人看到他进来都马上起身欢迎他。斯密招呼他们都坐下,皮特回答说:“不,在您尚未落座之前,我们不能坐下。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故事本身可能是捏造的,但皮特曾经认真研读《国富论》并深深为之倾倒却是真实的,他此后制定的政策、规定以及行政管理预算等很多方面,都闪现着斯密主义的影子,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打断其政策为止。
在斯密余生之年里,他倾覆心血最多的是其早期的作品。1790年,在斯密去世前不久,《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出版,与第一版相隔超过三十年时光。新版中有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包括增加了整个第六篇“美德的品性”。学者们对第六版的变化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增补内容对著作本身可有可无,只是澄清和细化早期版本中已经提出的思想。另一些人则认为,第六版中的新增论述极其重要,例如,第一次系统地讨论美德实际上由什么构成(而非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会称赞美德);强调商业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弊病,这种强调力度超越过去的任何版本;或者反过来说,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弊病,并提出了对治方法。探讨这些争论有可能让本文的尾声部分误入歧途,但肯定无疑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修订可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解读:向大卫·休谟的人生和著述致敬。
首先,几个新增段落与休谟著述中的一些睿智观点交相呼应。斯密对“体系精神”(Spirit of System)鞭辟入里的分析,呼应着休谟长期反对的思想政治立场。他对公民和宗教派系的批判也颇具休谟主义色彩。他宣称,“所有腐化道德情操的因素中……派系和狂热总是首当其冲”,这似乎可以呼应休谟在其论文和《英国史》中的大量类似论述。斯密对“中等和低等阶层的生活”和“谨慎的人”所具美德的赞美,与休谟始终坚称的商业社会是最有道德的社会遥相呼应。斯密反对以“恶意的嫉妒”眼光看待邻国的繁荣,这不仅延续了他在《国富论》中的观点,也延续了休谟早期有关“贸易中的嫉妒”观点。斯密有关自杀的讨论很可能是受到了休谟去世后出版的文论的启发。虽然,斯密并没有像休谟那样为自杀进行道德辩护,但他的确认同:“不幸的人以这种悲惨的方式毁灭自己并无不当,他们不该受到谴责,而应受到同情和怜悯。如果所有人类的惩罚措施都已经鞭长莫及,还要试图惩罚业已死去的他们,没有比这种不公正更荒谬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