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主流文化告诉我们,走慢一步会落后一大截,或者机会的流失都是源于自身没有掌握更先进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但实际上个人的处境始终是和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选择性行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倦怠”还是“积极”不能简单做两极定性。针对“全民倦怠”议题,《北大金融评论》“发展之路”栏目特邀世界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拉赫接受专访,她认为:“倦怠不是抑郁症,不应将其诊断为抑郁症,但它一定是来自对长期慢性压力源的管理。”
本文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5期。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这个时代针对身体的最大病毒,那么倦怠(burnout)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病毒。
倦怠不仅与新冠病毒同步,也是“后疫情”现象的次生放大。其实在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之前,倦怠已经是全世界最普遍、最令人焦虑的社会现象。最近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辞职,她的理由就是“我感到倦怠,没有足够的能量应对意想不到的挑战”。
倦怠不仅存在于工作和职场中间,也存在于家庭关系之中(比如夫妻关系或者家庭主妇的角色),还存在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各国之中,可谓是普世存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职场都流行倦怠文化,在中国,它的名字可能是“佛系、躺平、划水或者摆烂”;在美国,它的名字是“quitting” 或者“Great resignation”。当然,在美国的含义并不是要真要辞职,或者坚决离开现在这份工作,而是职场人士将用最小的力、最小的激情、最小的付出来应付现在这份工作。
对倦怠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开创性研究的伟大学者,就是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马斯拉赫出生于1946 年,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其出色的学术成为该系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教授,然后从该职位荣休(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的名誉教授)。马斯拉赫虽在诸多社会心理学领域都有建树,但在倦怠方面研究最为知名,被认为是“倦怠研究之母”。
社会心理学如何崛起?
在我们谈论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心理学的脉络,才能理解马斯拉赫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地位。
心理学是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的科学研究,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现象。这些现象都来自大脑,而大脑在现代科学中是可以测量的,例如用神经科学对脑区神经反应进行测量,所以心理学在学科上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心理学家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对大脑涌现出来的不同特性进行理解,比如知觉、认知、注意力、情绪、智力模式、主观体验、动机以及人格。这些特性又在不同的场景中展开,比如人际关系(人与人)、心理复原力(独处)、家庭复原(家庭关系)和社会心理(比如职场这样的社会空间)。当然,心理学不仅是研究,也可以作为治疗,解决人类的心理健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不仅观察、研究、寻因,而且还要治疗。心理学不仅是“理解”人类,还可以“改造”人类——这种改造当然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
现代心理学的起点源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于是他认为,心理活动就像微积分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就是程度的区别,都可以用微积分来衡量。哲学家康德不同意,认为“心理不可实验,也不可微分”,它是“灵魂的学说”,因为“有灵魂的人不会为了满足目的而接受自己被实验”,于是“心理观察本身已经改变被观察对象的状态”,这意味着心理学不可测量化。不过,康德的意见并非一言九鼎。费希纳(Gustav Fechner )和冯特(Wilhelm Wundt)是“心理测量”的狂热爱好者,尤其是冯特,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人类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心理实验的对象不应当是正常人,而应当是一些心理不正常的人,比如酗酒犯、暴力犯和“疯人院”里的家伙。所以,冯特的心理实验室最初其实是以不正常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随后才慢慢扩展到正常人群。
冯特开创的实验心理学路线,在英美落地生根,向全球扩散。跟随冯特学习的美国人Stanley Hall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心理学实验室。冯特的助手雨果·明斯特伯格 (Hugo Münsterberg)在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冯特的学生英国人爱德华·蒂钦纳,在康奈尔大学重新建构心理学课程,并提出了“结构主义”心理学,由此也推动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功能主义心理学。它结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创造出“意识流”一词,并对儿童的心理测试感兴趣,尤其是从幼儿期到青春期的心理测试。总之,康德的断言落了空。冯特的实验方法论是英美的主流,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冯特之外的欧洲大陆,是更加偏好康德的欧洲大陆,有很多心理学家不喜欢实验心理测试,试图找出一些独特的路数,比如抓住“康德关于人的目的性和社会性”这一命题,认为人的心理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的原型,一个是社会的塑造。于是,精神分析在1890年代崛起,代表人物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创伤性压抑是原因,而社会则强化了原型的焦虑,本我是原型,自我是体现,超我是塑造。弗洛伊德和他的欧洲弟子开创了自由联想和释梦的方法。由于他们用更加深层的(所谓对无意识的理解)话语体系来分析人的黑暗面,既带来猎奇效应,也带来感同身受,但是,它依然不太像科学,很多英美世界的实验心理学家觉得精神分析的结论和实验数据极不相符。对于现在的美国心理学系来说,弗洛伊德理论已经彻底被边缘化,沦为“历史文物”。
不过,弗洛伊德理论也有余音,它催生了“反向运动”,即完全颠倒了弗洛伊德的结论,建立所谓“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抛弃性焦虑、童年创伤这些东西,回到康德的“阳光面”,积极地看待整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人格的零散部分或孤立认知。例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他认为,“人都是上进的,都会摆脱黑暗的过去,人有主观意义,关注积极的成长而不是病态的延续。而且人是有雄心的,人是有需求层次结构的”。还有马丁·塞利格曼这样的积极心理学家,他们关注是人类传统中的“积极向上”,比如孔子很积极,佛陀很至善,基督懂得舍己为人,这些伟大的传统一直塑造着积极的人民,所以,人类心理学的主流应当是积极的,是可以自我提升的,而不是弗洛伊德式创伤的。
思想学派之间的竞争只是心理学发展的一条主线,演化出更加技术化学科化的脉络,比如从生物角度的认知神经科学、从后天角度的行为主义、从认知角度的认知心理学、从达尔文角度的进化心理学、从技术角度的临床心理学等等。但另外一条更重要的主线就是被社会所影响——确切地说,是被强大的政府力量“盯上了”。比如在苏联时期,苏联政府认为巴甫洛夫实验中的“刺激——反应”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定律,是否可以用于对人民的改造?给人民怎样的刺激,让人民成为应该成为的人民(新民)?尤其是在早期儿童阶段的教育。于是,苏联特别强调社会土壤和儿童研究,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以及用心理学改造那些“旧人”。美国也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委托罗伯特耶基斯对其180万美国士兵进行心理测试,识别出这些移民后代的忠诚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成为美国心理学主要资助者,其主要目的是:增强社会信心,克服共产主义者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影响。最著名的计划是19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CIA) 合作的心理战研究。
在第二条主线的影响下,心理学就开始拥有了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参与和社会改造性,于是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就横空出世。社会心理学将人类行为解释为心理状态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思想、感受和行为发生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变量如何影响社会互动。
这就是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毕生耕耘的范畴。
马斯拉赫“传奇式扭转”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197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19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经历了政府的要求之后,出现了自我学科化的“界限感”。其中,最重要的界限,就是与社会学进行“重新分工”:社会学家侧重于对社会进行高层次、大规模的考察,而社会心理学家通常侧重于对个体人类行为的更小规模的研究。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塑造所形成的心理问题——例如认知失调、旁观者干预和攻击性举止,提出了全新的范式,即情境主义:人类行为根据情境因素而改变。
一石激起千层浪。情境主义推翻了很多过去稳定的东西,比如稳定的人格、稳定的偏好,一个环保主义者在某个情境下也会随手丢垃圾,就像一个温和的好人被激怒了也会去杀人,一般性态度并不总是特定行为的良好预测指标。社会心理学就开始研究这一切是如何变化的。
一个举世瞩目的研究项目在1970年代诞生: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这个项目的资助人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他们经常被美国监狱里面存在的警卫和囚犯之间的冲突所困扰。囚犯似乎更有恶意,再温和的大学毕业的警卫也变成虐待狂,双方都呈现出越来越可怕的反社会倾向。于是,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委托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来做这项“斯坦福监狱实验”(注:该实验科学性存在争议)。

津巴多先从男性大学生被选中75人。经过心理健康实验后,被随机分配到位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中担任“囚犯”或“看守”。囚犯被限制在黑色钢条门的牢房中。每个牢房里有一张婴儿床,单独监禁则是没有任何光线的小壁橱。实验的角色分类,让同样大学生变成了不同的人,遵守不同的规则,行使不同的权力。津巴多本人则扮演“监狱长”的角色,调解看守与囚犯之间的纠纷。他定位自己是“温和的典狱长”,让看守想用不暴力的方式去控制囚犯。但实际上,他并不阻挡严重的看守虐待行为,例如剥夺那些不听话的囚犯的睡眠。实验越到后期,看守变得愈加咄咄逼人,拿走了囚犯的床(让他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强迫他们使用放在牢房里的水桶作为便桶,拒绝清空水桶。津巴多还是没有任何干预。看守知道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观察但没有受到斥责,他们认为,这就是“实质性允许”,于是他们就愈发变态去折磨囚犯——这些人其实是他们的同学。而有些囚犯开始受不了,但是根据规则,他们不能退出,于是有人假装患有抑郁症、无法控制的愤怒和其他精神障碍,最终获得假释。这名囚犯透露,假装“精神崩溃”就是为了早点离开。
实验第六天,一切都愈发紧张,因为看守中有人已经殴打囚犯,有囚犯绝食抗议,然后被看守单独关押了三个小时(尽管监狱实验的规则是只能关押一个小时)。其他囚犯大多数都不同情这个囚犯,认为他是坏囚犯和麻烦制造者,应当被严厉对待。囚犯和看守适应了他们的社会角色,超越了预期的界限,就像真的现实一样,人越来越进入“脚本情境”所设定的角色。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目睹了这一切,她当时是津巴多教授的女友,后来成为津巴多教授的妻子。她明确告诉津巴多教授,“这一切必须扭转,必须结束这个该死的监狱实验”。因为,“情境对我们人类行为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更强大。人在情境下会成为野兽,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马斯拉赫对情境主义的分析,彻底“扭转”津巴多的研究路线,也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了斯坦福监狱实验,让其阐发为人类最重要的心理实验。津巴多和马斯拉赫将这个实验所表达的情境主义称之为“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路西法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但是他堕落了,成为堕落天使。“即使是天使一样的好人,也可以被诱导、引诱,以邪恶方式行事。当他们沉浸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他们会以非理性的、愚蠢的、自我毁灭的、反社会和盲目的方式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个体的性格、道德稳定性和一致性感觉,都纷纷不成立。”
马斯拉赫和津巴多还认为,好人做恶是一种不断滑坡的过程,他们会沉浸其中。首先,这些好人不假思索接受社会规则,迈出“被规训的第一步”,然后会将他人视为非人类,可以在社会规则要求下随意对待,再通过体制的力量“去个性化自我”,从而分散他们的个人责任、任何时候都表现出盲从权威、不加批判地遵守群体规范、在事件的过程中,通过不作为漠不关心来容忍邪恶。最后,社会悲剧产生,所有人都变得邪恶。
这也是暴民政治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产生的社会机制。
马斯拉赫“扭转”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但是她注意到真实世界的监狱警卫以及去为囚犯辩护的律师们,都拥有一种稳定的(难以用情境主义解释的)的东西——倦怠。很多律师告诉马斯拉赫,“我付出了 110% 的努力,结果却发现自己痛苦不堪。如果我可以干点别的,我一定会转行的。而且,我会建议我的孩子远离那些该死的囚犯。”律师之外,医生护士、中学老师、的士司机、技术工程师们,都有这样的普遍状态。比如有技术工程师接受马斯拉赫的采访时表露,“我热爱我的工作。我是一个狂热的学习者,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但我的职场很糟糕,它鼓励同事之间的竞争、背后捅刀子、八卦。我发现上班很困难,回到家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马斯拉赫甚至发现家庭主妇也存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有很多人告诉马斯拉赫,“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我无比厌倦厨房和我的老公,我无比厌恶家庭主妇的人生”……就像“路西法效应”来自于圣经,倦怠(burnout)则来自莎士比亚在1599 年创作的十四行诗中,诗句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爱燃烧殆尽,她对男人不再拥有任何意图”。倦怠就是让人感到极度疲惫、愤世嫉俗、疏离感以及无能为力,这会导致他们在工作上、社交上和情感上退缩。倦怠就像莎士比亚的诗句那样,“曾经炽热的爱的火焰已经化为灰烬,留下的是筋疲力尽的感觉。”
马斯拉赫关注到倦怠是一种稳定的强大的潮流,1970年代是这样,21世纪更为强烈。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描述他们的工作危机、精神危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真正抓住倦怠的核心理解,倦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克服它?它是一种精神障碍吗?它有怎样的分析维度?
首先,马斯拉赫在1981年开始设计评估倦怠的工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Maslach 职业倦怠量表(MBI)”。无论是国际巨头还是国内的大型公司,在它们的员工工作系统里面都会集成MBI,员工经过评估后决定自己要不要找心理医生或者向上级主管讲述自己的状态。MBI设计的核心就是理解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在职业环境中对其他人缺乏同理心)。情绪耗竭,是激情的消失,而人格解体,则是受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发,人因为工作或者权力情境被“异化”成一个漠不关心(照章办事)的人。
其次,马斯拉赫并不确认倦怠是一种精神问题,倦怠并不是抑郁症。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就以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为例,很多人苦苦支撑他们的事业却最终感到筋疲力竭,相当部分人得了抑郁症,导致全球抑郁症药物的使用数量暴增。但是,马斯拉赫受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影响,她认为“人变坏是因为情境,如果中止这个情境或者改善这个情境,那么人会变好,这个过程不是人得了病,而是人受到了情境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医疗实验也证明了马斯拉赫似乎是对的。倦怠和抑郁症有重叠的症状,但从内分泌角度显示疾病的生物学基础是不同的。对倦怠症患者不应使用抗抑郁药治疗,因为这些药物会使潜在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恶化。
最重要的是,马斯拉赫建立一个综合体系来理解倦怠,就所谓“六因素评估”:“超负荷工作(工作量)、缺乏控制、奖励不足、社区崩溃、缺乏公平、价值冲突”。所以,当组织出现倦怠的时候,应当考察工作量是否合理?员工获得的资源是否充分?组织的价值观是否正向?对员工是否公平?领导是否存在霸凌现象,以及同事关系是否友善?
马斯拉赫希望自己对倦怠的研究,就像历史上英国煤矿工人下矿时带着金丝雀,这种鸟对危险气体的敏感远超人类。如果金丝雀死了,矿工便知道井下有危险气体,需要赶紧撤离。
马斯拉赫的研究就是这只“金丝雀”!
《北大金融评论》:马斯拉赫教授,我们仔细阅读了您与合作者写的书《倦怠挑战:管理人们与工作的关系》(The Burnout Challenge: Managing People'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Jobs),在您的书中,您认为职业倦怠主要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脱节,尤其体现在六个维度上面:工作量、控制、奖励、社区、公平和价值观。组织中谁应该解决这种脱节呢?是首席执行官吗?但是从组织的绩效评定上,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公司内部的倦怠,而是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股东利润。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我们的理论并不是关注脱节问题,这不是描述组织中员工正在发生什么。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工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当这种关系不匹配或不合适时会发生什么,这些不匹配代表了形成倦怠的长期工作压力源。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找到改善匹配的方法,以便让员工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让他们的绩效更棒。
所以,我们认为,从CEO到一线经理的组织都应该致力于解决不匹配问题,因为倦怠对组织来说代价非常高昂。为什么?倦怠会导致缺勤率增加、生产力降低、人员流失率增加,以及医疗保健成本增加。《哈佛商业评论》中有篇文章估计,在美国,与职业倦怠相关的年度医疗保健支出在1250 亿美元到1900 亿美元之间。另外一些研究表明,经历过倦怠的员工不仅更有可能请假,而且他们请假的时间是一般员工的两倍多。高流失率会让代价更加高昂,因为雇用新工人涉及更高的转换成本。关于工作与人不匹配的长期效应,还有一本书值得推荐,《为薪水而死:现代管理如何损害员工健康和公司绩效》,这是一本讲述倦怠如何对经济和人类生存底线产生负面影响的好书。作者是Jeffrey Pfeffer,在斯坦福商学院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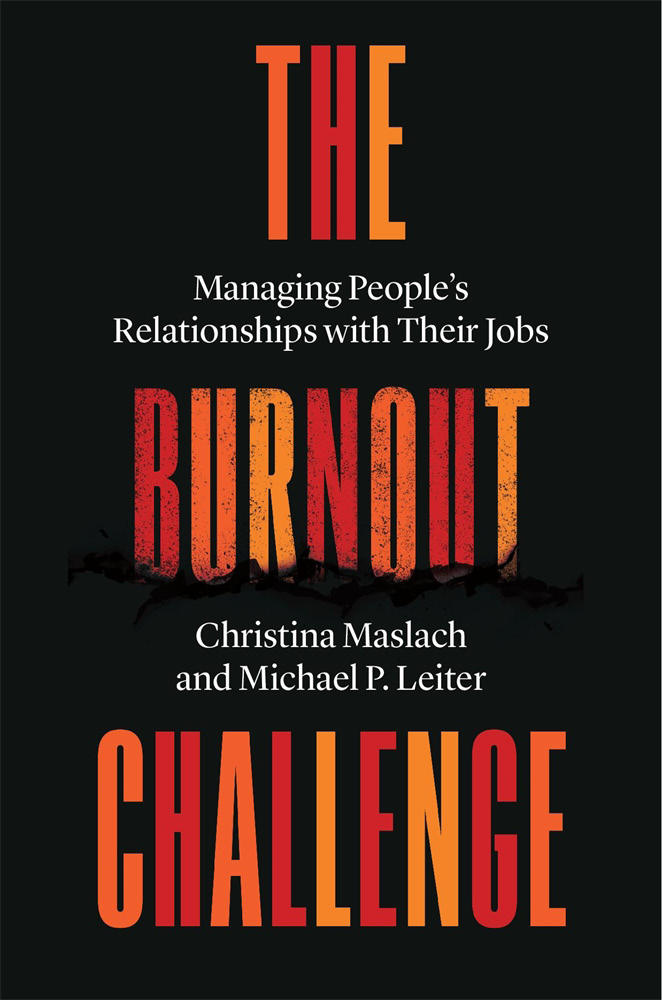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倦怠是一种基本生存危机。员工在长期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时会遇到这种情况,当工作环境与他们的需求和愿望不匹配就会产生倦怠,这在所有不同职业中都是一致。也许不同职业在加剧倦怠的“不匹配方面”有所不同,比如说,解决倦怠这种不匹配,对于医疗保健行业中的医生和护士或者技术公司里面的技术人员来说,要比销售人员更急迫。
《北大金融评论》:您怎么看待中国“996”现象背后的倦怠?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让员工“安静退出”背后反映了工作环境特征对员工的不尊重,以不切实际的要求和不健康的工作强度带给员工过度的负担,从而减少了他们的休息(非工作)时间。我在书中也专门提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所面临的“996工作文化”(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下班,每周必须工作6天)。这对员工来说非常不健康,非常不公平。他们用“躺平”只不过表示他们需要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更多的休息,为自己工作之外的个人兴趣腾出一些时间。所以,从我的倦怠理论分析(6要素)来看, 这里最不匹配的是“工作超负荷、缺乏控制和缺乏公平”。
我们对倦怠的研究,需要确定员工不同的工作经历。有的是倦怠,有的是与敬业度相反,比如说“脱轨”——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因为倦怠而产生非常强烈的愤世嫉俗,看不惯公司的一切(他们不一定是筋疲力尽或效率低下),会对公司工作条件进行冷嘲热讽,这往往导致工作绩效发生变化。员工只会尽力做到努力的最低限度,而不是尽力而为。它与“安静退出”或“躺平”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是故意、主动采取敌意策略),但它也反映了慢性工作压力源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从而产生“脱轨”。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接着谈谈中国的现实。因为职业倦怠(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失业)很多人变成了抑郁症患者,中国有大量这样的案例。虽然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职业倦怠与抑郁症不同,不过,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处于抑郁状态无法完成工作而非常弱势,他们过得非常糟糕。尤其是新冠全球大流行,导致中国人曾经因为防控、病毒对健康的冲击而变得痛苦抑郁。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不得不使用你创建的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MBI)来量化员工的职业倦怠,越来越多的公司设立心理咨询师。您觉得这种组织内部已经形成的干预,是个好办法吗?
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几个对倦怠的隐含假设,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们想先澄清一些基本常识。首先,世界卫生组织(WHO)对过去四十年的职业倦怠进行研究回顾,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职业现象”,最终会导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问题,但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医疗疾病。它与抑郁症肯定是不同的,所以不应将其“诊断”为抑郁症,也意味着不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治疗师进行治疗。
其次,世界卫生组织将工作倦怠定义为对“尚未成功管理的慢性工作压力源”的反应。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高压力的疲惫、对工作的愤世嫉俗,以及职业低效能感。当人面临威胁或挑战时,压力反应是人类机能的正常部分,不应被视为病态。然而,对于人们来说,最难的是从高频且持续的慢性工作压力中恢复过来,换句话说,工作场所的压力总是存在,躲也躲不掉。当员工长期承受这种压力并感到倦怠时,员工健康自然不佳,而且还会导致工作绩效不佳、旷工和离职。对于组织而言,意味着优秀员工的流失(雇用他们的投资回报率变得很低),同时也反映出人员流动的高成本,以及难以吸引新员工。
通过帮助员工应对压力源(例如提供心理咨询)来予以应对,当然是一种好意,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倦怠发生的原因。 倦怠的原因,是长期的工作压力源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防止倦怠实际上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仅仅是员工跟不上苛刻的工作节奏所造成的个人困难。
使用我所开创的马斯拉赫职业倦怠量表(MBI)来识别“谁”正在经历倦怠?实际上是对MBI的误用。相反,MBI旨在通过将其与其他工作条件的考察进行结合,从而发现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倦怠?如果以这种方式使用MBI,并与员工“共享”根本原因,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解决长期工作压力源以及如何更好地帮助员工管理它们。所以,MBI最终的目标是提高员工与工作的匹配度,让他们工作得更好,获得成长,而不是被打败。
这就是我最近出版《倦怠挑战:管理人们与工作的关系》的主要关注所在。我们在书中描述了工作与人匹配或不匹配的主要领域,并讨论了如何在可持续的道路上进行改进。无疑,这涉及如何更好地管理慢性工作压力源,如何改善工作环境。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比在倦怠发生后试图治疗更具建设性的方法。
(注:接受我们采访的不仅有马斯拉赫教授,还包括她的合作者阿卡迪亚大学心理学兼职教授迈克尔•P.莱特(Michael P. Leiter),所以,我们用“Maslach & Leiter”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在这里予以提示。)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即享超值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