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官方微信/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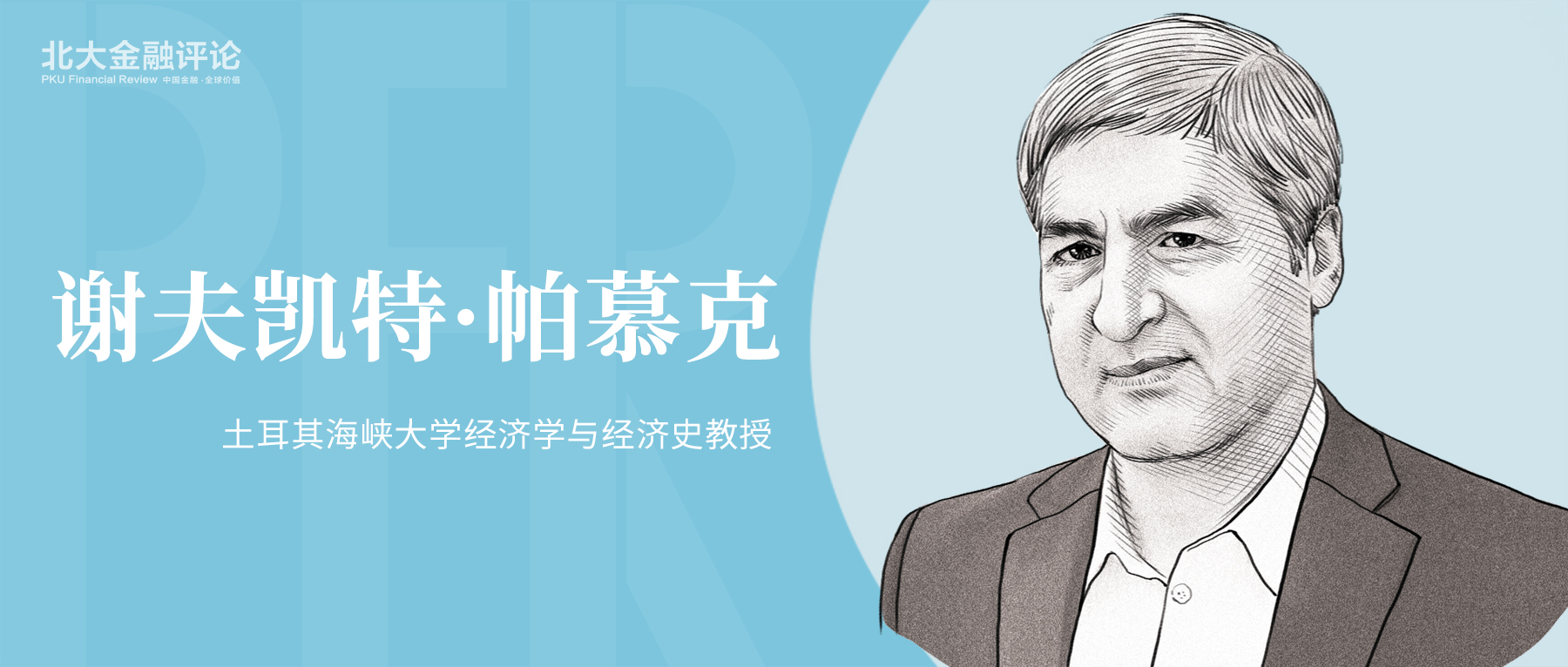
一战让奥斯曼陷入千年未有大变局之危机。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后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民族独立,废除列强瓜分土耳其全境的《色佛尔条约》。尽管失去了欧洲和中东的大部分领土,但签署了保留小亚细亚民族根据地的《洛桑条约》,保存了寻根之地。他以乌古斯土耳其人作为本体,不愿意将伊斯兰教作为本源,他甚至让土耳其学者提出“早期苏美尔人是原始土耳其人”来增强民族渊源的神话叙事。凯末尔非常痛恨奥斯曼伊斯兰体制,认为它是土耳其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西方化”是重生之道,于是,凯末尔将“伊斯兰宗教符号完全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将宗教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凯末尔严厉告诫民众和他的军人盟友:如果有政治家敢于表露亲近伊斯兰的姿态,必将入狱;如果民选政客有谁敢引伊斯兰教入国家政治,军队必将政变。
凯末尔作为“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国父)创建了国家规则,但这一“世俗化、民主化”规则能否在土耳其健康运行,并不依赖国父的持久“遗命余威”。1938年凯末尔去世,土耳其进入“后阿塔图尔克时代”。凯末尔的亲密助手伊诺努(İsmet İnönü)执行了“相机而动的亲西方政策”,土耳其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到了战争末期,看到德国必败,顺势投奔英美阵营。冷战开启,则迅速加入北约,朝鲜战争则参加联合国军,获得马歇尔欧洲重建计划的资金……总之,伊诺努领导的土耳其躲避二战,押对时局,投对阵营,但是,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起色不大,主因还是战争时期,全球经济链条阻断,土耳其难以独善其身。

随着曼德雷斯(Adnan Menderes)选举获胜取代伊诺努出任总理,伊斯兰开始渗入政治。首先,选举政治靠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既然伊斯兰是官方宗教,大部分人都沉浸在伊斯兰文化里面,越底层的人沉浸得越深。选举政治需不需要考虑这些选民的文化背景?政客们会不会进行各种“伊斯兰话语联结”呢?当然应该,这是根本规避不了的现实。事实上,文化战早就存在于土耳其,白土耳其人(Beyaz Türkler)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人口,拥护世俗主义、启蒙运动、实证主义等价值观;黑土耳其人(Siyah Türkler)则是伊斯兰教义的忠实接收者,大多在小亚细亚农村地区居住。曼德雷斯之所以战胜国父助手伊诺努,难道不是利用了“文化战”,激发大部分民众内心的“伊斯兰话语联结”?
其次,土耳其世俗化的过程,是一个弱国的实践。凯末尔主义有着亲西方的基调,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消退和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耗尽,新的金主在哪里?土耳其已经是北约成员,曼德雷斯居然想到正在赶美超英的苏联,希望捞点卢布。毫无疑问,这是弱国的权衡性选择,再次,土耳其石油不多,却是东西方油管的必经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过路费,也为了在中东地区重拾奥斯曼过往影响力,为国家利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土耳其人就思考:是否应当重启“伊斯兰联结”,与更多的伊斯兰国家搞好关系?
曼德雷斯的“伊斯兰重启”让凯末尔主义的将官们感到愤怒,他们遵循国父的遗命,在1960年发动政变,严厉地处决了曼德雷斯以及一大批内阁官员。
守护凯末尔主义、拥有“政变权力”的土耳其军队,在西方语境中它是一个正义且进步的存在,但是,它也在不断蜕变。共和国建立之后,军方发动了四次政变,分别在1960年5月27日、1971年3月12日和1980年9月12日以及2016年7月15日,除了2016年政变之外,其他都成功了。政变之余,军方对政府的小型干预不断,经常能够将官员直接打入监狱。土耳其军队之所以如此强悍,除了国父遗留的权威,他们把持了国家预算,军费一直是国家预算的最大头。土耳其军队还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工厂、医院和贸易公司,为军方提供小金库。土耳其高级军官的子女很多都去国外留学,这惹起不少争议。
例如为自己岳父切廷·多安喊冤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他的妻子皮纳尔·多安(Pınar Doğan)就留学美国,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师。切廷·多安因为涉嫌参与推翻埃尔多安的“大锤政变计划(Sledge Hammer)”而被判刑,罗德里克说,审判的证据是不完整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切廷·多安之前就多次参加军方策划的政变——比如1997年军事备忘录行动(Military Memorandum),他是核心策划人之一。该军事行动迫使具有伊斯兰倾向的总理内克梅丁·埃尔巴坎(Erbakan)辞职,禁止其从政,关闭其任期内开设的宗教学校。
埃尔巴坎正是埃尔多安的政治导师,埃尔多安也因为在公共场合念了一首“伊斯兰主义的诗歌”而被判入狱十个月。毫无疑问,土耳其军队的预算掌控、西方人脉、政变冲动和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力,是土耳其政治生态中极为不确定的部分。离谱的是,土耳其的“里根总统”厄扎尔(Turgut Özal),他因为表露出愿意与凯末尔主义者仇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谈判,就无声无息地死亡了。普遍认为,军方的嫌疑最大。
世俗化与伊斯兰、民主选票与理念联结、频繁政变和政府更换,土耳其经历了反复政治震荡之后,军方终于遇到了最为厉害的对手——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出生于伊斯兰文化根基最深、但也是最穷苦地方——里泽省。他看到了凯末尔的悖论:用宪法和军队刺刀强行分割土耳其民族最底层文化与选票型民主政治的关系,绝对行不通。人民拥有怎样的文化情感,他们就会投出怎样的选票,国家需要怎样的现代化未来,就制衡出怎样的世俗性结果。土耳其既有着伊斯兰情感,也有支持世俗化道路的庞大人群。这就是葛兰主义(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的论述:拒绝伊斯兰政治哲学,主张宗教和世俗充分参与职业、社会和政治生活,反对“凯末尔式的分割”(尽管日后埃尔多安与他的精神导师葛兰关系决裂)。埃尔多安认为,对土耳其最重要的是如何内生性解决问题,产生强大的经济,带来更多的城市化和人口脱贫,将伊斯兰情感转化为民族自豪感和外交资源,遏制军方的政变能力,也要注意跟西方尤其是欧盟和美国搞好关系。
埃尔多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军队的目标是保卫世俗化、走西方之路,埃尔多安将计就计,以土耳其必须加入欧盟为契机,满足欧盟的社会治理要求为核心策略,用加入欧盟的标准来“控制”土耳其军方。比如,按照欧盟要求,军费需要控制,埃尔多安监督国防开支,控制军方企业,让军队预算变得小于教育预算;根据欧盟要求,禁止军事法庭在和平时期审判平民,允许一般民事法庭审判军事人员,彻底打破军方的特权;再比如,严厉惩罚军队里面的“凯末尔遗产强烈维护派”;严打“大锤政变计划”的所有参与者,用广泛株连的方式来清除军队里面的“刺头”,让文官政府控制军队,而不是军队依靠枪来指挥政府。埃尔多安非常成功,把军方压制到建国以后前所未有的弱小地步。不过,在西方媒体上,埃尔多安被刻画成一个跟西方精神格格不入的威权人物,因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凯末尔主义的限制,他是奥斯曼帝国的精神继承人。”

通货膨胀的政治动力学
凯末尔建国之初,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太多认知。他对传统农业国土耳其的经济是自卑的,一个劲引入西方资本,改造国内经济是他的第一选择。凯末尔不断修新法,允许外国公司和外商在土耳其无限制投资。无论是土耳其西边的船运、东部的铁路、小亚细亚的矿业,还是银行业(英法控制的奥斯曼银行甚至起到了发行货币的央行作用),都被外资控制,而土耳其的民族经济,依然农业为主。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全球大萧条逆转了土耳其的思路,凯末尔惊奇发现苏联似乎没有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左翼经济学似乎是对的。土耳其政府放弃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扩大政府对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随后二战爆发,全球经济完全崩溃,土耳其未入战局,但经济也完全停滞。
1950年加入北约,享受马歇尔计划,土耳其进入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外资重新涌入,土耳其开始“三来一补”的初级制造业代工。其时,民选政府依然是跟随潮流思想,以“进口替代”来打造民族经济。经济的本质是“逐渐交换”而不是“一下就能学会”,“进口替代”问题在于,是否可以通过进口产品和技术,来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从而替代外国企业。土耳其“没学会”,不能产生可以与外部世界交换的产品来换取外汇,那么,土耳其的“进口替代”就是一个泡影。事实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反思“进口替代”的错误,它们经济弱小,不能自己长大,必须先依据全球分工格局,根据比较优势,赚取自己在这个阶段的辛苦铜板,再顺势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来分化出自己的动态优势,或者看准投资培养出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放弃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
“进口替代”积累出巨大的危机,进口多出口少,赤字巨大;里拉币值高估纯属“自嗨”,外部融资(外债)膨胀出现偿还危机,石油危机导致通胀迅猛上升,人民苦不堪言。最终,土耳其还是根据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将“进口替代”调整为“出口导向”,放弃无效的国有化而实施大胆的自由贸易,放开了外汇制度。主政的厄扎尔总统甚至提出一个口号:“要不出口,要不死亡”。土耳其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强健的增长,尽管增长有快有慢,但还是非常强劲,一直延续到埃尔多安时代。
尽管经济势头不错,但人们开始发现土耳其经济有两个顽疾:通货膨胀以及里拉贬值。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并不一定孪生的,比如中国在2005-2015年房地产飙升年代,有明显通胀,但人民币整体也是升值。土耳其作为一个正常经济体,居然长期跟通胀相伴,可谓奇哉怪也。
1960年代,1美元大约是9里拉,1970年代变成14里拉,1980年代是80里拉,1985年是500里拉,1990年是2500里拉,1995年是43000里拉,2000年是62万里拉,2005年1美元则达到135万里拉。金额大成这样,当然要“缩水”,土耳其2006年开始用新里拉(Yeni T ü rkliras)币值来置换旧的大额面钞(缩减了6个0),与美元的比率关系全年平均是1.3:1。好景不长,新里拉继续贬值,几乎延续了老里拉的势头,目前在27:1附近浮动。
当然,发生很多戏剧性的情节。很多土耳其平民认为,土耳其里拉永远都会贬值是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一些犹太人组成的秘密组织所为,他们是想让境内的基督教势力控制土耳其。西方主流媒体则认为是埃尔多安的“神奇经济学”所致。埃尔多安认为:降低利息是可以降低通胀的,因为降息会让经济增长更快,生产物品更多,从而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降低通胀,当经济增长越多,土耳其的里拉就会越强劲,从而扭转贬值的趋势。埃尔多安的“神奇经济学”是一个笑柄。没人能解释为什么获得世界平均增长率的土耳其会无休无止地遭遇到通胀和贬值的折磨,出产众多且出色经济学家的土耳其,一直在“赤字、利息、贬值、债务”上争吵不已,没有标准答案,无法形成共识。
回到帕慕克教授的主线认知,依然是“政治”。政治是人心,政治塑造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模式是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宏观工具包。因为“白土耳其”与“黑土耳其”的存在,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让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也是未来局势的起点。“白土耳其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受益者,他们的经济行为更好地融入西方,他们从房地产、纺织、汽车、旅游、建筑工程中获益赚到钱之后,对伊斯兰氛围不断强大的土耳其感到不舒服,他们将钱基本上都存为美元。土耳其储蓄中超过一半是美元存款,这意味着土耳其里拉在国内富裕人士眼中是不靠谱的。这不是埃尔多安时代才存在的现象,在厄扎尔总统时代就已经有了。对币种的态度,本质上是人的预期判断,在土耳其的自由兑换货币制度下,美元被抢购,回流到美国的债务市场。过多的里拉不断进入土耳其现钞市场,造成持续的通胀,以及兑换币值无止境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