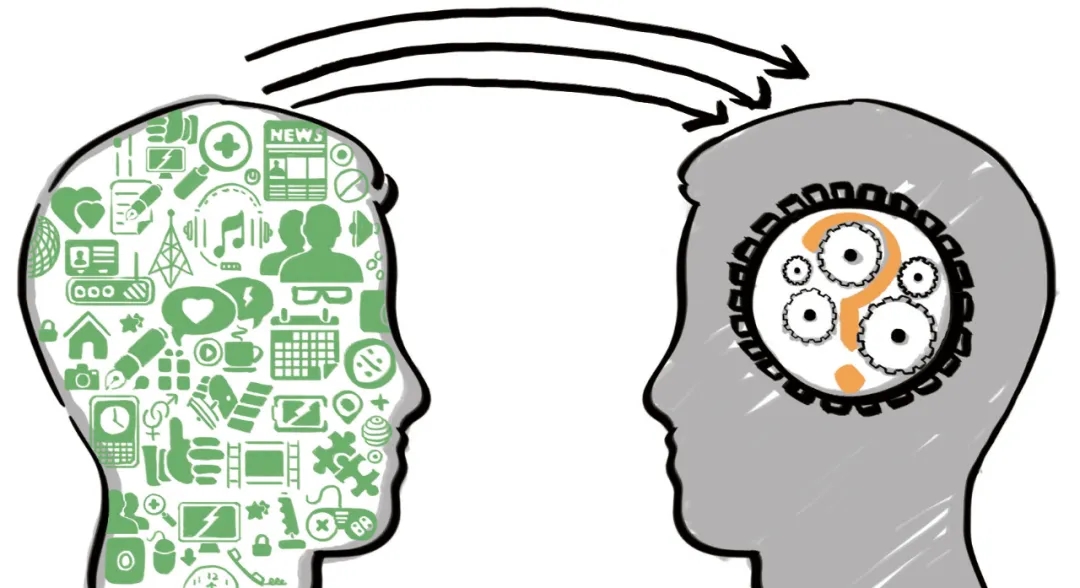参加一场讨论会,到最后总结阶段,原本一直在旁沉默的领导也受邀说说自己的看法。他开始谦称“是来学习的”,推辞不过才“随便说两句”,然而他一开口就仿佛精神焕发了,竟然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而所谈则天马行空,有很多都是从讨论的议题“发散”出去的,以至于他讲完之后,底下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接。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景象也算是常态。人们之所以对“文山会海”感到头疼,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冗长的会议往往既没有产生预期的成效,也很少包含有效的信息,那更多是一种消耗人的仪式。这并不仅仅是官场习气,常常还渗透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
文化记者张畅曾说,她做媒体久了,见识了很多对谈、问答之后就知道,“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说空话和大话不停铺陈,重复,迷失,到最后什么问题都没说清,什么观点都没表达。这种说话和写作的方式,既不庄重也不优雅,甚至都达不到交流和表达的基本功能”。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低效率的沟通,付出的隐形社会成本很高,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她推测“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从教一个人说话开始,从没有要求一个人言简意赅、表达清晰、切中要点,更多的是为了应付考试炫技式地玩文字游戏”,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不止如此。
在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公共对话原本就是缺失的。考虑到小农社会的分散性和等级结构,再加上缺乏城邦社会那种公共空间,恐怕既没有“公共”,也谈不上“对话”——因为“对话”本身就预设了两个平等个体的存在,需要通过讨论、协商来面对或解决彼此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这样,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就只是“我说你听”的教诲,以及都不用说出来的那种“心领神会”。
原本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这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人们早已熟知你的为人、处境,本能地明白你为什么会那么说话。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不是表面上的单纯意思,而是一种复合的信息——尤其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结构之中,传达着权力的意味和复杂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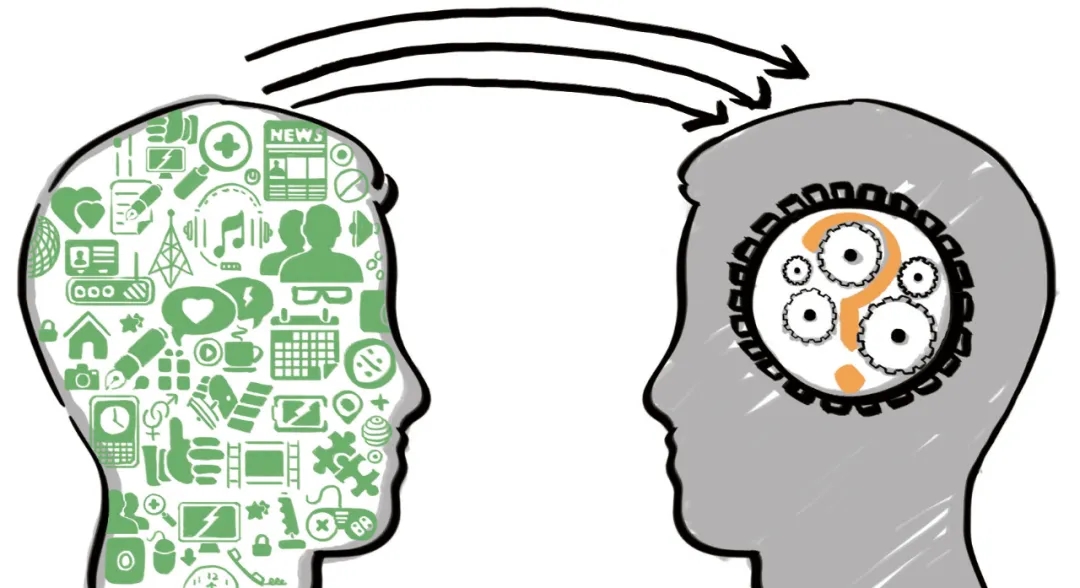
像这样的状况,至今仍弥漫在我们的公共话语之中。广为流行“内涵段子”,就是一种“内行才能看懂”的梗,你得代入那个语境,才能第一时间回味过来笑点在哪里;但等而下之者,就很容易沦为“你猜”,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和误会。由于很多话语都是这样藏头露尾的“半句话”,有时真正想传达的还不是有效信息本身,而是某种情绪碰撞,这也就难怪在我们的网络环境中充斥着无效沟通,往往需要撇开大量浮油,才能在底下看清楚对方真正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我发现,即便是很多高智商、高学历的人才,也常常很少去想自己研究的意义,如何体现其价值,又怎样向公众说明。有一位历史学博士曾说,他去海外留学时,曾想面试一个医学人文学的职位,对方抛出一个问题:“请告诉医学院的学生,为什么要来上你的医学史课程?”他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结果可想而知。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这样公共对话的传统,很多人都是埋头各搞一套,彼此之间对话很少,也不必向公众说明自己做事的价值,不用说服他人,也就没能学会从他人的角度来设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意义。这样,人们在潜意识里只是“我自己感兴趣”,最多就是说服自己相信“这有意义”,却不会预设面向哪些受众(有时还是外行的受众)言说,以至于说出来时往往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甚至说了等于白说的感觉,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想过哪些信息才是别人感兴趣的。
但在西方,自来就有面向公众演讲的惯例,这是必不可少的思维训练。在外企的二十年里,自入行起,得到的告诫便是,在写作任何一份提案之前都要自我设问:你想表达什么?想对谁说?对方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凭什么他要相信你说的这些?你想通过这个提案,说服他哪几点?如何才能做到?
当你习惯之后,就会觉得那都是很平常的基本问题,是在那种文化语境下几乎大多数人都会问的问题。然而,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却很少需要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挑战,以至于很多人会感觉措手不及,甚至明明可能做的事不错,却不懂得如何表达出来。
网络时代高度分散化的信息渠道,很可能又加剧了这样的困境,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从海量信息中判断,也不知道如何看待和应对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以至于原本应当是“观点的碰撞”,最后往往变成了抬杠式的“情绪的碰撞”。其结果,当下的中国人可能比父辈面临着更嘈杂的社会语境,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如何甄别有效信息上。
社会学者黄盈盈曾说,现在舆论场的嘈杂,不一定是人们对某件事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更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多元了,观点也多元了,人群于是分化了,而且你也看到了分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网络将个体拖进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人们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和自己不同的声音,这虽造成不适,但也会在不断的碰撞中迫使他们自我反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很多人来说,如何在限定时间内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是在社会转型期才大规模涌现的新问题。虽然当下的状况或许不尽如人意,但数千年来,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中学习如何对话。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作为平等独立的个体置身于公共对话环境中,进而充分意识到有必要面对大众说明自己的观点时,才能在不间断的日常实践中学会这一点。